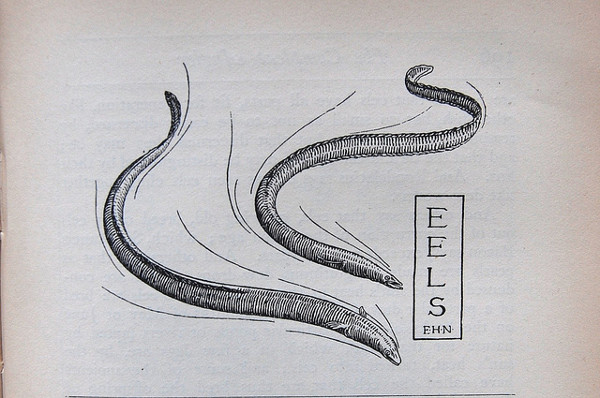看到杨花萝卜四字,很容易就想到汪曾祺先生,因为先生曾经写过;大概提到汪老先生,又很容易便会想到的应该是高邮的鸭蛋,因为那篇《端午的鸭蛋》在语文课本里收录着的,让人不由地印象深刻。
说来奇怪,阿青觉得苏教版的教材里似乎倒是未曾选录这一篇,阿青记得的是《受戒》和《侯银匠》,大概还有《陈小手》,有一年江苏高考用了《侯银匠》篇,接着的各校试题便纷纷绕不开汪曾祺这个名字了,连带着亦读了许多他的文章,觉得用“一支淡笔写出留在心底的人间至味”来形容真是毫不夸张。
杨花萝卜之所以叫杨花萝卜,大概是因为上市在杨花飞舞的三四月;然而阿青觉得每年过年的时候,饭桌上也会有一碟鲜红娇嫩的杨花萝卜,取的便是这红色以增喜庆,到了端午的时候,杨花萝卜亦是扬州地区“端午十二红”中不可或缺的。唤作杨花,使人不由地想到“杨花落尽子规啼”,诗意盎然,一下子就从许多的青萝卜、白萝卜、红萝卜中脱颖而出了。
杨花萝卜上市的时候,会有乡间的妇人推着小板车或是挎着小篮子来兜卖,萝卜连着叶一把一把的码着,时不时的洒一点水。杨花萝卜没有水的时候,其红便会显得灰暗,若是洒上了水便显得娇艳欲滴,叫人打心眼里爱它。扬州的主妇们会在回家的路上称上一些,临过年的时候杨花萝卜还是卖得很金贵的,因为家家户户都要买,便不复汪老先生文章里“给她一个铜板,她就用小刀切下三四根萝卜”那样的时代了;不过幸而杨花萝卜也并非用来煲汤炒菜,大多还是用来凉拌的,添个新鲜罢了,亦不需很大量。
小孩子喜欢在妈妈洗好萝卜后便时不时地去拈一个来生吃,杨花萝卜生吃很好吃,香甜脆嫩,富有水分,一丝丝萝卜的辣都尝不出来;每每把妈妈洗好了的偷吃得差不多了,便会听到妈妈的骂声:“小炮子哉,萝卜还要用来拌呢!”小炮子哉这种骂小孩的方式和杨花萝卜一样亦是扬州的特色,长大了不会再被骂了,还有些许的怀念。就像长大了再也不会馋到去生吃萝卜,偶尔尝一个亦觉得不如记忆中的好吃。大概小孩子总是容易满足的,小时候吃的东西总是极好吃,长大了后每每心中念想,但是真的吃到了觉得不如记忆中的味道,不免失望;觉得好吃也许也是为着那种明知会被骂还去做的惊险和刺激。
杨花萝卜用来凉拌,阿青不知别的人家如何,但是阿青家里是很少把萝卜斜切片再切细丝的,因为杨花萝卜本就个头娇小,富含水分,若是那样细细地切,水分便流失尽了,失去了它本身的很多鲜味;一般会像拍蒜一般用刀背将一个一个的小萝卜拍开,不至散,看起来像是盛开的红莲那般的形状,然后加麻酱油,醋拌上,再撒上一点细葱花,不仅颜色赏心悦目,吃起来也是别具风味。但是切片切丝的做法大概也是有的,那样摆碟子更显得整齐精致一些,但是于口味上难免会有欠缺。一个完整的杨花萝卜含着醋的挑逗的酸,酱油的鲜,麻油的香和萝卜本身的清甜爽口,多层味觉享受在舌尖依次打开,那种感觉无法比拟。
其实冬天里的萝卜除了杨花萝卜,其他萝卜也很是出挑,自古就有“冬天的萝卜赛羊肉”说法。江苏人喜爱用白萝卜炖汤,配排骨或是老鸭都好,汤白而醇,萝卜耐长时间的炖煮,不似山药容易糊汤,冬瓜又容易散烂。南京似乎出个头大的白萝卜,小的时候看小姑娘们跳橡皮筋,会唱“南京大萝卜”,《冶城蔬谱》中形容南京产的萝卜“硕大坚实,一颗七八两重”。
关于萝卜还值得一提的是萝卜丝饼和萝卜丝包子,汪曾祺在《萝卜》一文中提到“扬州人、广东人制萝卜丝饼,妙极”。阿青是一个小女子,中国的大江南北还有很多地方没有走过,广东这片土地便未留下阿青的足迹,以后去的机会大概也不会大多,所以也不知道现在还像不像汪老先生所说的那样,只是扬州的萝卜丝饼真的是好,萝卜馅有的湿有的干,干有干的好,湿有湿的好,入口都是绵绵甜甜。不过,阿青有一个同学,广东人,有一次一起吃萝卜炖羊肉,倒是提起过他吃不得萝卜,会肚痛;作家叶灵凤有一篇《蒙田三书》的文艺随笔,忽然宕开一笔,写到萝卜,说:“据我的经验,广东人对萝卜是不大有好感,至少是不爱吃,更不会生吃的。”那就是咯。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喜爱杨花萝卜的人呢,自然是想着多多益善的。
文/阿青
图/x.Rain.z循CC协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