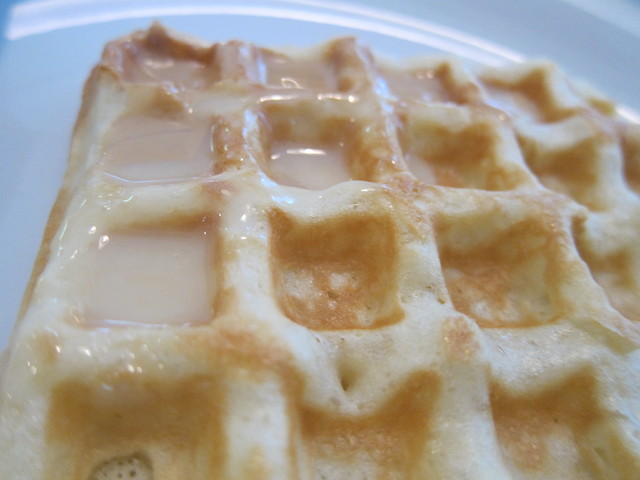一天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想是早餐时。七点的闹钟一响,便叮咚哐呛起床洗漱,在朦胧意识里准备妥当开始出门。下了寝室楼,顺着那条老道直直地走上两三百米,向左一转,便是个早餐摊点,左边是各种包点,右边是三大锅热着的粥。不记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便只在那一家买了,所以不多时,老板娘便认得我们这常客了,有时人多,见我们来了还会先尽着我们,这便是常客与生客的差别,典型中国人情社会的写照。
当然,这话说的往偏的方向走了。之所以每日定点在那家买早点,不仅感于老板娘的和气,也是被她家的烧卖给深深吸引了。每天早上必须得有一个烧卖,另外再配上一个甜卷,中和烧卖带来的深重味道,切断舌尖对烧卖的无尽想念。
一个热哄哄的烧卖可以开启我一天所有的味觉和触感。这家的烧卖不大,外边一层薄薄的面皮不紧不松地贴合在里面圆锥形的若隐若现的糯米团上,既不干硬难咬,也不黏腻松垮,总之是粒粒分明又口口干爽。里面包的糯米团大概是淋了酱油之类的,带着些酱汁的颜色,但是又分明保留着些糯米蒸熟后那种晶莹剔透的感觉,两种颜色揉和在一起,一粒粒糯米便成了两头尖尖通透圆滑,中间渐变成酱色的诱人风味,看相极好。
当然,单有外观也不值得如此钟爱,关键是那烧卖的味道极有回味的空间。老板娘应该是用猪油作为原料来蒸那糯米的,每每咬下一口,猪油所蒸出来的一种鲜香便包裹着粒粒粘合在一起的糯米充满整个口腔,将糯米的滋味包装起来,再一并推送出一种浓而不烈,香而不艳的滋味。
吃烧卖时不宜快速咀嚼,因为来自猪油的味道并不浓厚(若是油太重不仅腻人,影响刚刚苏醒的肠胃对早点的憧憬,而且也会把烧卖原有的自然味道掩盖,过犹不及),需要咬下一口,然后停下片刻,待舌头上的味蕾充分拥抱了食物,再慢慢咀嚼,在唾液淀粉酶的作用下,一丝一丝地化解这简单食物里最原始的鲜味,于是一口香甜一口顺滑,在对味道的满足中再将其送下,等待下一口的享受。
也许有人会说猪油蒸出来的烧卖定会很油的感觉,但是熟谙中庸之道的中国人自然懂得如何平衡食材中的各式滋味,然后以一种自然融合的方式让它们无失偏颇地组合起来,达到至臻完美的境界。动物油原生的滑腻自有那一层薄薄的面皮中和,那白白的面粉一揉一展一包一蒸,再送入口中,虽无本味,但又恰恰是这种空无的味道,使得对于油的滑腻有了化解之道,简简单单一道面皮,也许我们吃的时候根本感觉不到它的味道和作用,但是它就是包裹着这糯米,包裹着这油汁,在食物被送至下一个消化道之时,以它独特的性质将残余舌尖的油腻带走,只为下一口的品尝如第一口般清透,只为下一口的品尝如第一口般美好,将味道的相互增益相互烘托发挥至极致。
在一次次拥抱着烧卖之后,我的舌头终于在不尽的渴望和享受中"沦陷"。于是,每一天我的身体所消化的第一个美味便是那小小的烧卖。一个烧卖享用完毕,身体在味觉的带动下开始活动起来,怀着对烧卖味道的满满享受,思想也开始伸展舒张。一天的学习课程在吃完早餐后便正式开始了。
周末回到家里,时间充裕,早餐的式样便多了。对于食为上的我,早餐是必不会省下的,无论多晚起床,早餐也一定要做到实至名归。有段时间狂热地执着于面条,每天早上宁愿费些时间也要煮上一碗面条,或配上肉,或淋上蔡林记的芝麻酱,无比鲜美。偶尔打了武氏猪脚的汤给淋上,爽口至极。
吃了这么多年的面条,未觉有哪种面条本身的味道多么独特,但凡是好吃的面条均因有着一味好的酱汁或汤汁的加入,面条滑入口中的同时挂着汤汁的浓浓暖意和美味精华直送心间,然后一个响亮亮的饱隔将对食物的挚爱和满足尽数表达。或许这种对于食物的追求是种遗传,总之这一点上我与母亲是绝对一脉相承的,但是这并不代表着这种符合遗传学规律的生理特征就一定多么科学。
记得有一个寒假的早晨,我和母亲就着前一天在市场上买的重庆辣干的油汁下了面条,那一次的面条简直就是绝对的热辣辣,刚刚出锅的面条,汤面上浮着一层鲜红的油汁,热气携卷着辣干的味道铺面而来,一口下去,辣到不能自拔,味道应该说是好的,只是作为不能吃辣的我在面对这样的极品料理时就只能跪求放过了。时至今日,我都记得那样热辣辣的汤和欲尽而不能的那一碗热腾腾的浸润着鲜红辣汁的面条。
除了面条,家附近的德园包点也是极好的,除了油汁太过丰厚了之外。但是若没有那浸透面皮的厚油,德园包点的大肉包也许就落于平凡了。总体来说,我还是喜欢吃他家的大肉包的,但是一次仅能吃一个,若再要多吃,只恐会被腻翻。不知道德园大肉包的肉质如何,这个问题往往只有父亲才会考虑,但既然他也是吃的,那想必还是不错的。所谓大肉包,当然个头是有些分量的,其次那内里的肉团也是实打实的瘦肉,一口咬下去除了满足就是再来一口。
每次吃德园肉包,我总爱从油汁已渗透表皮的那一端开始,虽然明明知道那里的油太过厚重而容易腻,但是似乎吃肉包就是和吃烧卖不一样,似乎就是要追求一种被油腻到再也吃不下旁的东西的原始饱腹之感。与烧卖不同,这里的油汁是从内里包着的肉团里渗出来的,不仅有自己的原味还浸润着来自鲜肉和小葱的纯正味道,就像是炒菜时会结合各类食材的味道在火的作用下升华一般,当油汁带着其他两种食味从食材内部慢慢渗出时,不说别的,光是透过重重分子结构的过程就足以令人惊叹!
在最外层面皮的阻挡下,油汁不再渗透,透过光滑轻薄的面皮,能看到油汁将包子染成脆黄的颜色,顺着包子结构步步外延的油同时又在包子上留下了痕迹,慢慢的透过外皮顺着阳光的射线,那小小的网状结构清晰可见,于是带着心动一口咬下,狠狠地咀嚼,将包子里的油挤出,尝遍鲜味后满意含下,然后开始下一口对肉团的享受,最后带着一口肉的鲜香和一嘴黄油完成早餐的仪式开始一天的生活。
有一种早餐是只能在家里享用的,那便是豆浆。据说豆浆源于炼丹师的意外收获,那么老天一定知道我多么感谢它让炼丹师发明了这个流传千世的美味。南北方都有将豆浆作早餐的生活习惯,只是口味浓淡会有些不同,我所喜欢的豆浆,是浓稠的,是不需要加盐也毋须放糖的,我以为无添加的味道才能传递来自食材的原始享受,加盐或加糖或许让豆浆风味凸显了,但终究不是它原始的味道,拿来一品,也不算是真正的豆浆的体味。
许多人打豆浆都爱将豆渣滤出,但我家从不丢掉豆渣,留着多好,又不是废弃物,喝的豆浆也不过是被打得更细碎的豆渣和水实现了混合,大点的豆渣只是不幸没能实现完美融合罢了,营养依旧在。当然,我之所以爱将它们留下还是因为它们实现了我对浓度的追求,倒是不知道自己喜爱浓稠物的这一点究竟是随了谁呢。
各种豆子泡上一晚,然后加水,加上一些燕麦片加强豆浆的粘稠度,再加上些花生实现香味的跟进,按上按钮,数十分钟后,豆浆新鲜出炉,香味四溢,直接挑逗身体的每一处毛孔,一闻,所有毛孔尽数打开。滚烫的豆浆刚刚倒出不到一分钟,便在最上边形成一层膜,有人说这种膜不能食用,但是那喷香的一面干一面湿,送入口中又黏又滑的美味足以抗拒一切对它的不利言辞。吹去些热气后,一口豆浆一路从唇隙滑下肚,热热的,暖着内脏,香香的,直到肺腑,那一种享受,简直美到骨子里。
有人喜欢淡淡的豆浆,一杯下肚,口中清清爽爽,不沾丝毫。可我偏偏欢喜这浓浓豆浆留在口中的味道,太淡的豆浆喝下去就下去的,除了一丝丝香味,不一会就没了,但浓浓的豆浆就不一样,因着浓稠,味道也就不易消散,当肚子在享受的时候,嘴巴里还能久久回味那般热切香浓,满足感不减一丝,多好!
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经久流传,单说早餐也是说不完的,说到豆浆就不得不提油条,谈及油条就不得不提麻团,谈及麻团就不得不提锅贴……
各式美食,简单又多样,填饱了多少人的肚子,孕着这个民族的多少文化习俗。
所谓民以食为天,食末而一天始。
文 任月
图 avlxyz 循CC协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