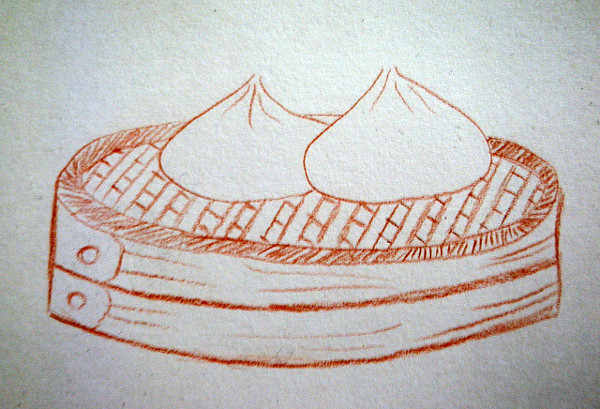用力生活,认真吃饭!
这句话,早在上学期开始之前就告诉过自己了,可是真真正正做到了吗?
每一天辗转于课室,宿舍,东区。三点的线性生活,稳稳固固的一天天堆砌成一大段的时光,最终集结,形成一把,矫情地冠上“岁月”,或者换一个活力一点的词,就叫“青春”吧。这样子的生活,开心吗?我只能说充实。就好像上发条的玩具,鲜活的生动,只是因为惯性。恩,惯性生活。那发条玩具惯性用完了,停下来了怎么办。忧患从不肯轻易舍弃我,所以我常常想多,想远。当然,也陷入循环式的漩涡。关于远方,担忧而无能为力。这始终是个没有结果的伪命题,就光施展个大气场,让人手足无措,慌乱心扉。
“看得到轮廓,测不透真切。团团笼罩,如同浓雾,压制呼吸,奔跑无向。”这样的感受无数次地汹涌上来,挟制到行动。人的向上力在这个时候就是最最薄弱的了。这时候,如果再加上个失眠,便秘,消化不良,或者再来一节根本就听不进去的专业课之后,整个人就完完全全被邪恶势力控制住了,患得患失。焦虑浸润到神经里,一个眼神,就洞察出煞气,大老远就已经嗅到旁人勿近的警告。这样的小娴娴,连我自己都嫌弃极了,还怎么去做一个充满正能量的人,怎么去感染众人,普渡众生,怎么去进行收复太阳运动,去拯救世界呀?我鄙夷把生活混成一团麻的自己,却连自已都陷入周期性的情绪当中。这时候,就算送一个和平星来帮我实现愿望也无济于事呀。
然而,日子一点儿也没有等你的意思,它呀,就是那么神气,撅着头,死拧死拧,吧唧吧唧地朝前走。心里头还得意洋洋地想着,哼,不走就算了,跟你斗,我就输了。
是呀,跟日子斗,就输了。小学课本里面那个跟时间赛跑的小娃娃不是早就告诉我们说,别跟时间赛跑了吗?都输掉了。偏偏你就固执得跟大黄牛一样样,不听话。输。怎么个输法呢?听着,时间就偷偷兑一点失忆水在你血液里,在你每一次情绪亢奋的制高点,最大化发挥效率,最后模糊掉你脑海里最初的景象。正是基于这个道理,我们念念不忘旧事,旧人。模凌两可的残缺,忘记掉了痛苦,留下的是久经咀嚼的甘甜,而味道嘛,自然是回味无穷。那么,进一步讲,现下的烦躁,都会被遗忘在未来。那么,你还有什么理由纠结啊。
我认真地思量了一下,匆匆,似乎是我惯性的状态了。放学了匆匆去觅食,踩着上课铃响起的时候匆匆进教室。直到某一天,忽然发现,那条每天经过无数次的路,旁边的风景都是我不甚熟悉的,更是未曾深入观察的。而就连吃饭都是急匆匆的。或许可以找个借口说是肚子饿到发抖,饿到没力气说话。但是,直到那天,我还是老样子,骑着小单车,匆匆地奔波在通往教学楼的沙路,又是即将迟到的临界状态,目中别无他物,终点就是课室,目的就是顺利到达去上课。可是在我前方是一辆四个轮子的车车,人家扬尘而去,毫不吝啬地非给我扬尘满脸的浪漫美感。突然,一个顿呃。我问自己,骑那么快干嘛?
“骑那么快干嘛?”前面还不是飞沙群舞在邀请你。走,那么快干嘛?生活。傻逼如我,走那么快,把生活都给丢了,又有何用?于是呢,从那天起,我对自己说,慢一点骑车,早一点出门,认真看一下走过的路,慢一点吃饭,一口一口地尝一下食物的用心,给肠胃一点时间去接纳食物。而事实上,走得慢一点,似乎路在变长。尺度拉长,把生活当成了放大镜,一丁点破事就让自己乐了很久,至于纠结呢?也消散不见其踪。我,踩在路上,此时看得见看不见尽头,都已经无所谓。路在,人小,拉远几个维度来看,恰好跳掉几个坑坑洼洼。
抵制焦虑,慢一点生活。尽管我知道,用力生活,从认真吃饭先开始!曾有一段时间,夜不能寐,食不知味的低潮期,整个人就阴暗得如一滩泥,扶不起来。熬夜,肠胃君相当抗议,恶性循环。那时候才切身理解“身体是革命的本钱”。连最基本灵气的物质载体都抗议了,拿什么去长征。而,此时他人再多的安慰,不过是隔着靴子在挠痒痒,无法深入痛处。或许我比较悲观,我信仰的是自我救赎。所以呢,当最终我发现肠胃差到调中药都没有效果,医生嘱咐说没事多运动时,我忽然滋生出莫名的欲望。这股欲望鞭挞我去和生活割据相抗,我就不信,没有谁不能统筹好生活。温暖,是自己给的,生活,是自己选择的。
一直很喜欢林徽因的一句话,“各自认取个生活模样。”只是偶尔没有“成全”好自己。而在这个极端坏的状态下,自然衍生出朝向好的方面转化,简单说,就是“否极泰来”了。下定了决心,抗争三座“大山”,失眠,消化不良的众多肠胃病。每天开始了喝蜂蜜水,吃红薯,日本若素片调和,泡脚,煲红豆薏米水的高强度活动。容易水肿的体质,从煲红豆薏米水开始改变吧。
红豆,薏米。祛湿神物。至于效果,听起来有慑人心魄的动心。但是因人而异吧,还有贵在坚持。许多事情都是这样子的,压根就不知道有没有作用,都是像骗小孩子一样的,必须认真地尝试完,还不给你明确答复,非得等有一天让你豁然开朗地明了,呵,原来在不知不觉间答案分晓,效果显著。这样的过程,迟疑,是等待。心动,是结果。
学生宿舍的局限性,功率就死卡在八百瓦之内。幸好人的创造力无限。我最大化地应用了电动中药煲的功能。每天晚上临睡前,一定会淘洗好红豆,薏米。取水些许浸泡好红豆薏米,让它们熟悉熟悉中药煲的构造。第二天起床,马上通电煲红豆薏米水。药煲是陶瓷材质的,材质上让人舒适,不排斥。完全不像不锈钢那般急躁让人反感。而只要时间充足,水量够多,红豆薏米自然在适宜情况下酝酿好芬芳,索引人于鼻翼。人事物,不一样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吗?就像张爱玲笔下那一句,“原来你也在这样啊。”天然无粉饰,自然靠雕琢。我可以做的只是等待。而最性感的姿势,莫过于红豆吸足水,胀破了肚子,沙沙的纤维质溢出,融在了水里,充实了水的生命。这个瞬间有如少女的初眸,其实质却是新妇的娇媚。薏米呢,久经焖煮,自然更是胀大了身肢,在水里开了花。如花的薏米,慢慢熬出一股黏黏的质感,和上染上红豆生命力的汤,袅袅升腾的气息,刚刚好足够温暖。盛一碗这样的汤水喝下去,咕噜咕噜,小口小口的吞进喉咙里,下达肠胃。汤,不是水水的状态,是带着高一些的溶质,密度略大,温度略高,需要小心吹气,一点点滋润。以水带水,祛湿的功能,我想大概是一种怀柔政策,红豆和薏米的精华溶解在汤里,带到身体里,去和那些多余的水妥协,做好协调工作。当然,效果就是,洗手间跑得频繁了,水排出了,人轻松了。哈哈。身心轻松,皆大欢喜。
妥协,柔弱的抗争。我想也不失为妙计吧。于是乎,我喝红豆薏米水,喝上了瘾了。许多时候,别人给不了,安慰不了的难受。不如,自己煲一锅红豆薏米水,好好温暖安抚身体里的水吧。心一轻松,自然走得舒畅了。只是别忘啦,走一点,就好比砂锅总是好过不锈钢的冷冰冰吧。别忘了,路上的风景。晚安。不小心熬夜了。恩,用力生活,认真吃饭。
文 红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