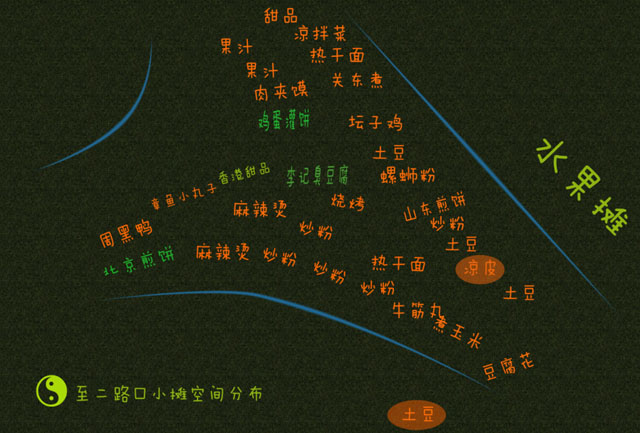下班的时候总是很晚。
常常走很远很远一段僻静的路,到一家饭馆炒一份扬州炒饭,然后穿过这个城市常常下雨的阴沉的天空,回到自己孤踞在二楼的房间。
有时,在路上会碰到一两个匆匆走过的行人,他们灰暗的脸庞上没有任何表情,就这样迎面走来,搅起冷潮的空气,然后擦身走开。
有时情不自禁会想:在每个人隐忍的面容后面,都会有不同的际遇。有的如平静的湖面,终日没有一丝波澜;有的像山涧溪流,生活里总有些愉悦的浪花;有的则是澎湃的海洋,一生起伏跌宕,埋伏在他旅程上的,是数不清的暗涌和礁石。
于是微笑。
但是却全然看不出什么。他们默默走过,各式的面孔在迷离的灯光中一闪即逝,如同晨雾中显现又被吞没的花朵。
而这城市却是一色的灰。偶尔一两片树叶在灯火的照耀下会突然明亮起来,却又瞬间幻灭,覆没在夜色深深的浪中。
只有饭馆是热闹的。厨房灯火昏暗,热气腾腾,许多翻动的锅里飘出世俗而幸福的香味。餐厅明亮而整洁,三五成群的人在吃着这城市香浓的羊肉或狗肉火锅。有时也会有一对对的情侣。或者,他们张扬地说笑,向这里炫耀在他们内部茂盛生长着的爱情;或者,只是安静地对坐着吃饭,在把关的一刹深情相望,然后,满脸幸福地低下头去。
而这一切都不属于我。
绕过一条长长的僻静的路,行经这城市常常下雨冷潮的天空,爬上五楼长而阴暗的楼梯,听自己的脚步声在空旷的楼道中寻找回音,回到自己孤踞在二楼的房间。我,要去咽下我的一碗炒饭。
回到房间时,饭就已经半冷了。嫩黄色的米饭中间杂着红黄绿各色小颗粒,却并不互相粘连。据说扬州炒饭的米饭要煮得粒粒松散、松硬有度才有口感,而在这个城市,则一律用冷饭代替。虽然不及淮扬菜肴原汁原味,却也颇有异曲同工的意思。拿起筷子一尝,果然松散而有嚼头,每一粒都相象,每一粒都自成一体。
忽然想起自己和路遇的行人。同在一片天空下,都表情平静地行走在一条街上,却各自有自己的空间和心情,像极了一碗孤独的炒饭。
其实细想起来,炒饭真是孤独者的专属。融融一家人,早餐吃和和美美的面条、松软的包馒头或者是细腻的豆浆稀饭,中午是各色丰盛的美味,晚饭再加一个热闹的火锅,至于那饭不饭、菜不菜的炒饭,除了孤独的人,谁想这么简单而匆促?
于是细嚼孤独。
记不起是谁的歌缓缓流过:“……有时候交谈变得空洞、沉默却像沟通、孤独可以寂寞、也可以是自由,能安慰自己的人比较容易快乐……”
君子其实应该独处,但“慎独”却也非常必要。孤独太多容易伤神,只有学会安慰自己,才能乐观而又沉静的品质。
孤独的炒饭吃多了容易胃滞,那么就加点酸甜快乐的乌橄榄吧!虽然没有品尝过,但是想到一个人在夜幕沉沉的城市独自咀嚼孤独的时候,心里还拔节着思念的温暖,我的嘴角就已经隐隐地渗出了笑意。
文/易小婉
图/Harvey Jiang 循CC协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