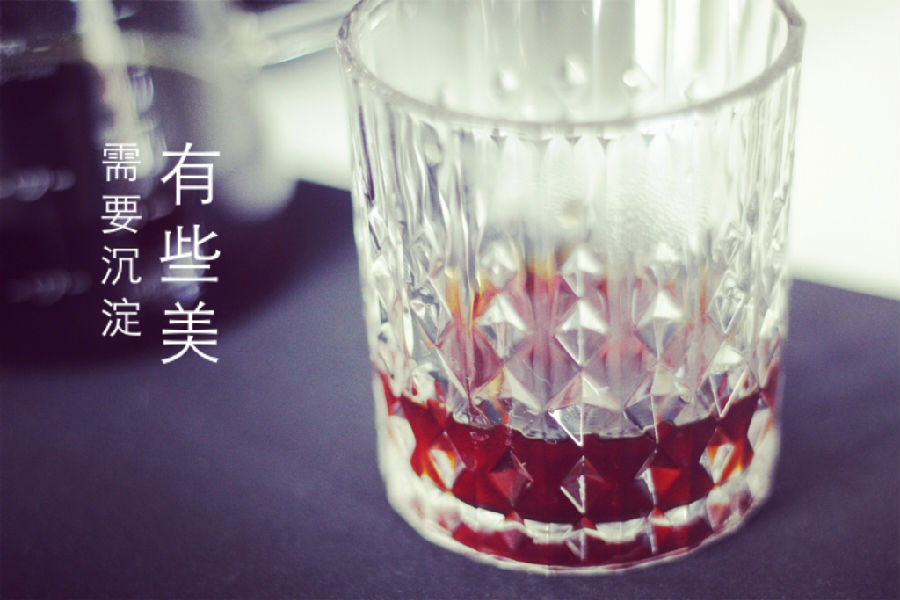我的家在桂林,说到桂林,自然少不了米粉。任何一个桂林人,只要坐进店堂,顾不得矜持,“呼啦啦”风卷残云,连碗里的汤也要喝得精光。看到北京街头的“桂林米粉”,忍不住去尝了一下。想来碗卤菜粉,居然没有,很是失望。也许北方人更倾向于汤粉,不喜欢干捞,即使是吃卤菜粉也要加一大碗汤。
Miss应是喜欢桂林的。盛夏的傍晚,暑气散去,坐着电单车在桂林的大街小巷穿行,空气中弥漫着香樟的味道。桂林人早餐吃什么呢?她问我。米粉。中餐呢?米粉呀。那晚餐呢?还是米粉。
没错桂林人的一天是从米粉开始的,但却没有结束的时间。通宵营业的米粉店周而复始地述说着这座城市对于米粉的热爱和依恋。
Miss应十分不解桂林人对米粉的痴迷,直到第一次亲身尝试,便一发不可收拾地深深爱上了这个味道。她喜欢在米粉中加各种佐料,特别是辣椒和酸豆角,一碗米粉里有半碗是佐料,尽管堆得高,那双筷子还是可以上下自如地在碗里翻转而不让佐料掉出来,看来她吃米粉的天赋是与生俱来的。
一碗地道的桂林卤菜米粉是怎样的?需配了锅烧、牛肉巴、叉烧、卤肠、卤肝、卤肚、卤舌、卤喉等八种卤味,少一种就不成其为卤菜米粉。同时还有五种素配,黄豆、椿芽、葱花、芫荽、蒜米。而且这五种素配还有严格的要求,卤菜米粉春天配黄豆、椿芽,夏天配黄豆、葱花,秋天配黄豆、芫荽、冬天配黄豆、蒜米,不能多也不能少,更不能乱配,以求米粉口感的最佳适度。
锅烧要用上五花,皮要炸得又酥又脆,肉又不油腻。黄豆炸出来,放三天也不会疲软。牛肉巴要有韧劲,有嚼头。是那卤水,就更讲究了,春秋两季要放浓香、咸鲜型。夏天放清香、甜鲜型。冬天放浓香、辣鲜型。
配米粉的油也非常讲究,要用猪板油和老干姜先武火,后文火慢慢熬出来。
早晨一碗米粉吃下肚,中午打嗝还可以“口吐兰香”,余味悠长。那切卤菜的刀工也要十分了得,片片卤菜,都要切得和纸一样薄,提起来透光透亮,鼻孔出气也能吹动它。只有这样,那卤水、香油的味,才能迅速渗透到肉体里头。
桂林老一辈人吃米粉,拌粉的时间要比吃粉的时间还要长,就是要让卤水、香油、卤菜的味好好综合起来,吃起来才津津有味。
米粉,是桂林的倾城之恋!
文/石头
图/Sam 循CC协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