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书时看到有这个词:Spiced Pumpkin Seeds。看到时愣了愣,转念一想,这不就是五香南瓜籽吗?
没想到在书里看到了英文版的这个词,中文版都忘了多久没有听过了,更忘了多久没有吃过这种儿时的小零嘴了。在这个物质丰富年代,普通百姓已经很少炒南瓜籽来吃了。反而若是去一些高档的餐厅,会炒来放在一个精致的小瓷碟里,当饭前小吃。

这个朴实无华的小零嘴,牵动着我和爷爷的一段独一无二的回忆。追忆起炒南瓜子这份童年味道,眼前浮现的,是爷爷拿着锅铲在柴火炉子边,躬着身子一遍一遍地翻炒着南瓜籽的画面。
小时候,家庭条件真的不如现在好,也许没有什么山珍海味,但来自于大自然的免费美味便足以动人。而这炒南瓜籽,就是爷爷小时候给我们几个小馋猫的特制解馋小吃。
 那时候的家里的某个角落,总会存着几个南瓜,就像冬天的菜干一样,当做“备胎菜”,以备不时之需。每次煮南瓜时,爷爷都会事先将裹着南瓜籽的瓜囊掏出来,在清水里耐心淘洗,只留下一颗颗南瓜籽。
那时候的家里的某个角落,总会存着几个南瓜,就像冬天的菜干一样,当做“备胎菜”,以备不时之需。每次煮南瓜时,爷爷都会事先将裹着南瓜籽的瓜囊掏出来,在清水里耐心淘洗,只留下一颗颗南瓜籽。

冲洗干净的南瓜籽,颗粒饱满,白白胖胖的,好不可爱。爷爷把洗好的南瓜籽铺在竹子编的簸箕里,稍稍晾干。每次看到簸箕里的南瓜籽,我们几只小馋猫就知道:“有好吃的啦!”

炒南瓜籽看着简单,却是个需要耐心的活计,食材的新鲜与火候的把握缺一不可。柴火炉子上架着一口大铁锅,南瓜籽随着锅铲上下翻腾。爷爷一遍又一遍地翻炒,好让每一颗南瓜籽都能受热均匀。南瓜籽里的水分被逐渐蒸发,带出果仁特有的油脂香气。
爷爷捻起少许盐,再撒些五香粉,纯粹天的果仁香便染上了几分家常的烟火气了。南瓜籽的香味是高调、爱炫耀的——这咸辛的滋味,飘出了爷爷的小厨房,飘进了在门外眼巴巴等着的我们的鼻腔里,也会窜出屋外,去撩拨路人的肠胃。

刚出锅的五香南瓜籽,热气腾腾,香气四溢,几只小馋猫早在厨房门口列队一样等着了。可惜,印象中若是南瓜不大,炒好的南瓜籽只得一碗,爷爷怕我们抢,会分同样多给我们。
我们双手捧成一个小碗状,爷爷就一撮撮地放进我们的小手里。刚出锅的南瓜籽还是热辣辣的,可就是不愿意撒手。看着手心了躺满了白白胖胖的南瓜籽,会傻傻地哈哈大笑起来,仿佛得了什么了不起的珍宝。
 小心翼翼捧在手心里,平时走路都是像个兔子一样蹦蹦跳跳的,可是因为这喷香的南瓜籽不得不迈着小步子走。几只小馋猫一起走到小朋友群中,看着大家艳羡的眼神,心里美滋滋的。
小心翼翼捧在手心里,平时走路都是像个兔子一样蹦蹦跳跳的,可是因为这喷香的南瓜籽不得不迈着小步子走。几只小馋猫一起走到小朋友群中,看着大家艳羡的眼神,心里美滋滋的。

直到吃完最后一颗还不忘记舔一舔手,把残留在手中最后的一丝香味都吸进腹中,才心甘情愿。然后,在心里期待着:“要是下次家里开的南瓜大一点就好了。”
后来长大了,这柴火炒南瓜籽再难吃到。有时馋虫来了,去超市买了那种纯五香瓜子仁,十来块便有满满一袋了。初食倒是过瘾,可再也没有那种珍惜的感觉。后来,也试着上网搜了教程,看起来是蛮简单。

可到最后,我也没有做。
因为时过境迁,拿锅铲的人不是爷爷,锅也不是那一口锅,味道肯定不是记忆中那般了。不要说我懒得做,而是味道真的是有记忆,我不想骗它。








 我和老徐坐在重庆南山上一家占据了整个山头的火锅店,我们的一侧是咕噜咕噜翻滚着的重庆火锅,还有满满一大桌子的菜,另一侧则是漫山遍野的火树银花不夜天。
我和老徐坐在重庆南山上一家占据了整个山头的火锅店,我们的一侧是咕噜咕噜翻滚着的重庆火锅,还有满满一大桌子的菜,另一侧则是漫山遍野的火树银花不夜天。 加入醪糟和白酒熬制的牛油,如一块上好的凝脂玉,在热力中被慢慢融化。馋嘴的我用筷子尖蘸了少许红油,舌尖触碰到尚未变得滚烫的红油,带来电流流窜一般的麻痹感。但丝毫没有想象中的腻人,反而是香而不腥,有着莫名的爽快口感。
加入醪糟和白酒熬制的牛油,如一块上好的凝脂玉,在热力中被慢慢融化。馋嘴的我用筷子尖蘸了少许红油,舌尖触碰到尚未变得滚烫的红油,带来电流流窜一般的麻痹感。但丝毫没有想象中的腻人,反而是香而不腥,有着莫名的爽快口感。 终于,整个锅底都在热烈地翻滚,深不见底的红油底下的花椒和干椒都在暗流涌动。可作为一个口味清淡、容易上火的广东人,我理智地选择了将鸭肠放进了白锅里。
终于,整个锅底都在热烈地翻滚,深不见底的红油底下的花椒和干椒都在暗流涌动。可作为一个口味清淡、容易上火的广东人,我理智地选择了将鸭肠放进了白锅里。 老徐瞥了我一眼,二话不说在红锅里涮了鸭肠,夹到我碗里,用毒贩子引诱无知少女的眼神看着我。我颤颤巍巍地将那鸭肠夹起来,吃了下去。
老徐瞥了我一眼,二话不说在红锅里涮了鸭肠,夹到我碗里,用毒贩子引诱无知少女的眼神看着我。我颤颤巍巍地将那鸭肠夹起来,吃了下去。 我果断放弃白锅,投入红锅的怀抱,迫不及待地逐一将鸭肠、毛肚、黄喉、午餐肉、猪脑放进锅里,新鲜的食材们马上和汤底融为一体,像在汤底下在手拉手跳一支《天鹅湖》,只闻气味不见其身。
我果断放弃白锅,投入红锅的怀抱,迫不及待地逐一将鸭肠、毛肚、黄喉、午餐肉、猪脑放进锅里,新鲜的食材们马上和汤底融为一体,像在汤底下在手拉手跳一支《天鹅湖》,只闻气味不见其身。 合计着时间到了,便忙不迭地捞起来,我蘸上早已蠢蠢欲动的香油、蒜蓉和蚝油配制的酱料,稍微一搅就放入口中。肉质的鲜美还沾着红油的刺激、干椒的辛辣、配料中蚝油的那一丝丝甘甜都被温柔地包裹起来,刚柔并济地撞向你的喉咙和舌尖,像在一个寒夜里狠狠扑向你的热烈拥抱。
合计着时间到了,便忙不迭地捞起来,我蘸上早已蠢蠢欲动的香油、蒜蓉和蚝油配制的酱料,稍微一搅就放入口中。肉质的鲜美还沾着红油的刺激、干椒的辛辣、配料中蚝油的那一丝丝甘甜都被温柔地包裹起来,刚柔并济地撞向你的喉咙和舌尖,像在一个寒夜里狠狠扑向你的热烈拥抱。 作为在广州这座美食之城长大的好青年,曾经一度以为全国各地的美食都可以在羊城遍地开花的餐厅里吃得到。对于重庆火锅,虽也向往,但是也没有太过期盼。结果从第一顿开始,我才发现,假如有人不爱吃火锅,那肯定是没有吃过正宗的重庆火锅。
作为在广州这座美食之城长大的好青年,曾经一度以为全国各地的美食都可以在羊城遍地开花的餐厅里吃得到。对于重庆火锅,虽也向往,但是也没有太过期盼。结果从第一顿开始,我才发现,假如有人不爱吃火锅,那肯定是没有吃过正宗的重庆火锅。 彼时是我和老徐分别在各自的城市里,在被如小山般的工作文件淹没之前,用十分钟订好了机票酒店,周末就拖着小箱子来到了千里之外的山城。
彼时是我和老徐分别在各自的城市里,在被如小山般的工作文件淹没之前,用十分钟订好了机票酒店,周末就拖着小箱子来到了千里之外的山城。 就连我们在向一对情侣询问火锅一条街怎么走的时候,他们都在指路之后严肃地加一句“千万别吃第一间!不好吃!”说完自己都笑了起来,手拉着手很快跑开了。我们注视着他们欢快的背影,感觉重庆人的热情已经穿越了云层,连月亮都被震动。
就连我们在向一对情侣询问火锅一条街怎么走的时候,他们都在指路之后严肃地加一句“千万别吃第一间!不好吃!”说完自己都笑了起来,手拉着手很快跑开了。我们注视着他们欢快的背影,感觉重庆人的热情已经穿越了云层,连月亮都被震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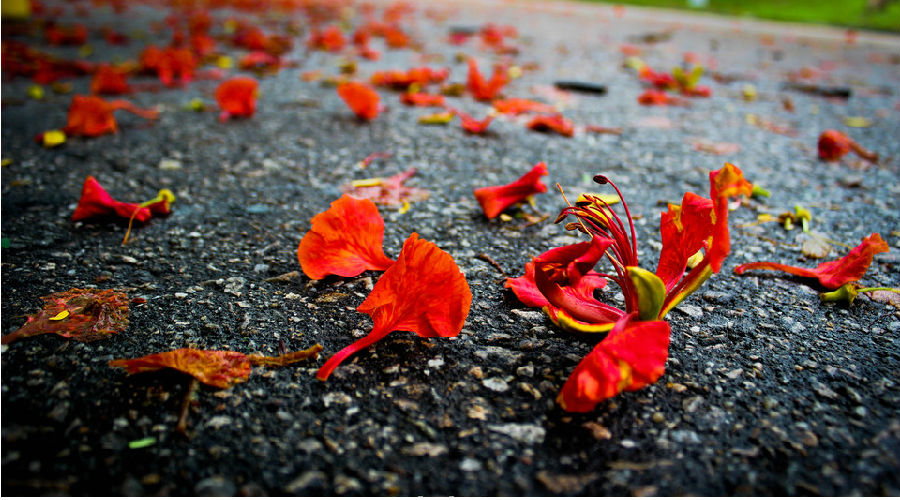

 蠢笨的个头,莫名坚硬且难剥的外壳,坚韧弹牙如皮蛋,蛋白竟然还自带分层。更不用说外层发青、内里掉渣,口感令人联想到粉笔的老口蛋黄……
蠢笨的个头,莫名坚硬且难剥的外壳,坚韧弹牙如皮蛋,蛋白竟然还自带分层。更不用说外层发青、内里掉渣,口感令人联想到粉笔的老口蛋黄…… 想打打牙祭的话,我会跑去市里的轻食店,叫份班尼迪克蛋沙拉。可层层蔬菜上窝着的那颗漂亮的水波蛋,往往又因为从厨房到餐桌这短短几分钟的冷却,透出点腥气。不由得让人暗暗觉得,这花出去的几十大洋有些划不来。
想打打牙祭的话,我会跑去市里的轻食店,叫份班尼迪克蛋沙拉。可层层蔬菜上窝着的那颗漂亮的水波蛋,往往又因为从厨房到餐桌这短短几分钟的冷却,透出点腥气。不由得让人暗暗觉得,这花出去的几十大洋有些划不来。

 迎着迅速冷却带来的白汽,我迫不及待地把蛋捞出,用餐刀小心翼翼在半腰磕出一圈缝,双手捏住两端,然后轻柔地豁开缝隙——一汪水波蛋跃然眼前!
迎着迅速冷却带来的白汽,我迫不及待地把蛋捞出,用餐刀小心翼翼在半腰磕出一圈缝,双手捏住两端,然后轻柔地豁开缝隙——一汪水波蛋跃然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