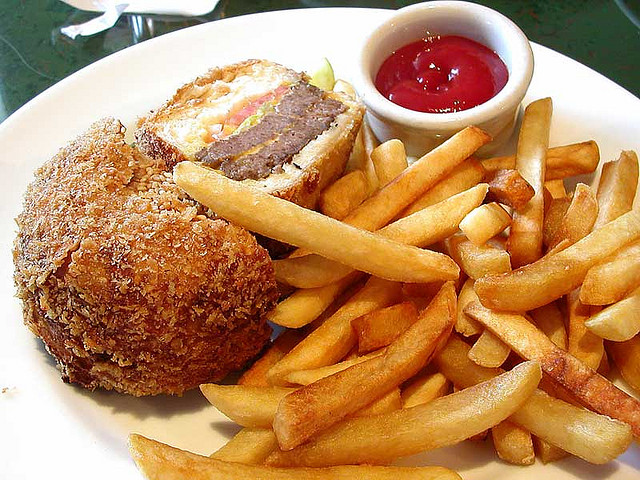小时候吃面条鱼的次数屈指可数。为什么呢?因为比较矜贵。记忆里,家里来贵客或远方亲戚,小孩子才能跟着吃上几口。而且那还必须是春天回暖三四月份,面条鱼靠近渤海岸来甩籽,渔民才有得打,市面上才有得卖。妈妈那时候都是用面粉裹住它们用小火慢慢煎,以保留它原来的鲜嫩,到嘴里软软的。自小就爱吃鱼腥的我于是牢牢记住了这种鲜嫩美妙的滋味。
妈妈说,他们小时候住在哈尔滨,松花江春天回暖就出产这种鱼,早起用来下面条,真是鲜嫩无比。面条面条鱼分不清,可是嚼到嘴里不同凡响!
我能想象那种滋味。爸爸是海员,小时候我们去大连探望他,那时候大船停泊在外锚地,每天晚上,爸爸都会用白色胶布缠在鱼钩上,伸到海里去钓乌贼。然后直接用来煮面吃当宵夜,什么佐料都不加。可还有比那个更鲜美的面条吗?至今还在怀念。
定居广州后,几乎对海鲜失去了兴趣。从小吃惯了渤海湾的鱼虾螃蟹,觉得南方的海鲜如同嚼蜡。都说北方的海鲜更鲜美,是因为有寒冬的缘故,让肉质更筋道,我认为极是。不过现在有快递这玩意,还很普及,真是利民利我。妈妈每年都会从秦皇岛寄来各种干货,还有熟面条鱼。妈妈用鸡蛋裹住煎熟,多放点盐,用最大号保鲜盒密封好,走航空一天就到我家冰箱。我们每天早上用小火煨热来吃,以解馋虫。不过那也只限于春天,每年只一次。
去年国庆带女儿回秦皇岛。除了惯常必有的濑尿虾螃蟹,妈妈又端出来一盘热腾腾香喷喷的鸡蛋煎面条鱼。我欢喜之余才知道,妈妈春天用空矿泉水瓶冷冻了好多,就等我回家吃。
今年冬天回家,临走时,妈妈突然到处找棉花碎布,说想用它们来保温,把一瓶冰冻的面条鱼让我带回广州。我说路上气温高恐怕会变质。妈妈还是坚持说试试。后来回到家,已是深夜,我直接就把矿泉瓶塞到冰箱冷冻层。直到下一个周末,我终于有力气按照妈妈的指示,把还在冰冻状态的矿泉水瓶直接用刀剁开,解冻,然后混了鸡蛋液,放点盐,用油煎熟,那熟悉的味道又来了。女儿抱着盘子,一口气全部吃完。那一刻,真是觉得好幸福。
有时候,我却很自私地,并不希望吃面条鱼的频率变得频繁起来。就像美好的事物总是稀有,太频繁,便会磨损那种兴奋。不如让我一直有所怀念,有所期待,那面条鱼的幸福滋味。
图&文/刘雨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