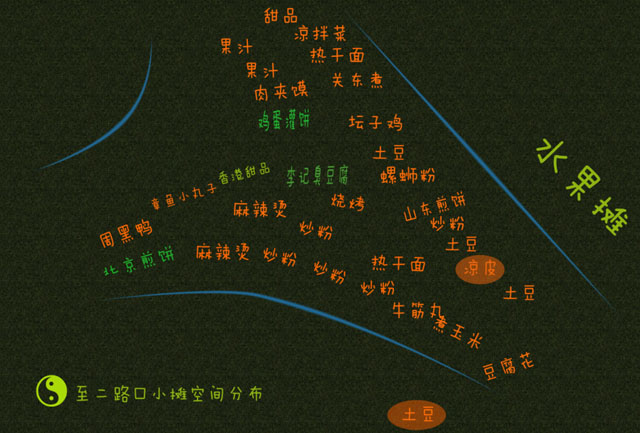清明的一场雨,将内心的燥热洗刷得干干净净。
趁着清明的假期,穿越了成都的大街小巷,凌乱的菜市场,安静祥和的小区,相似的场景,如同四五年前刚离家读书的那个春天,一样的清冷寂寞。大概,那是到现在十八年里最难熬的几年了哟。那时的我,还没有学会怎么好好一个人生活,所以,总是很难受的。人,或许也是这么成长起来的。
不要责怪那时的我。因为,毕竟从小就是待在父亲母亲身边长大的。那时的清明也会坐海哥小时长途客车回家,只为可以在父母身边暖一暖。清明,似乎?没有吃青团的习惯,但是,我会心心念念的是和父母从扫墓后山上采回的蕨菜。
清晨便带好鞭炮,纸钱,肉,糖果,香火去给老太太扫墓,湿漉漉的野草打湿你的鞋子,扫完后有时母亲和姨会去山上寻找蕨菜,或者是父亲骑着摩托在清明假期带我和母亲去兜风,去摘蕨菜。蕨菜就是蕨类刚长出来的嫩芽,叶还没有舒展开,带着一层绒毛,摘下手上黏黏的感觉。约莫半个小时便可摘得满满一大袋子,母亲总是笑着说可以吃好几顿了。
关于蕨菜我最喜爱吃的莫过于两道菜,蕨菜炒腊肉和清炒水蕨菜。蕨菜炒腊肉是用的山蕨菜略带点紫红,将腊肉煮软,放入葱姜蒜辣椒煸炒出香味,再放入蕨菜炒熟,红红的五花腊肉搭配新鲜的蕨菜,既冲淡的腊肉的油腻和咸味又注入一份新的鲜香。吃一口蕨菜,扒两大口米饭,感觉得温暖而满足。内心的孤独,也在和家人的团聚中渐渐消失 。清炒水蕨菜也是春末夏至常吃的一道菜,只是蕨菜不是长在山上而是在水边,因而颜色也是清清爽爽的绿色。水蕨菜比山蕨菜小根也更嫩个,撕成小条,清炒,吃起来滑滑的略带涩味却又不是涩味,在吃完大鱼大肉之后来一盘清炒水蕨菜是极好的。
寒假返校父亲送我去车站的路上,天气是极好的,初春点点绿。母亲说,再过不久,我们就再开车出来玩,这个山边一定会有蕨菜,还有那个竹林里,我们去偷点春笋。我和父亲总是会嘲笑母亲没追求,只会图这些小惠小利,难怪干不成大事,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初中老师。殊不知,一家人在一起,一个个小小瞬间组成的便是最大的幸福。
大城市里很少见到蕨菜,偶尔见到也卖得很贵,不知为什么,明明是山上到处都有野菜。这时候心里就会扬起满满的自豪,卖这么贵,我可是吃过好多好多。
又是一年清明时,和父母一起踏青的日子一去不复返,我长大了他们却老了。
甚是想念这味山珍。想念依偎在父母身边的日子。
图&文/劲哥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