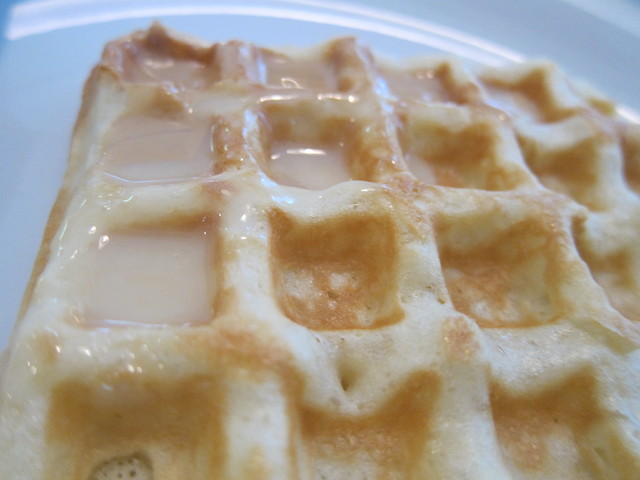读大学那几年,寒暑假回家,先坐40多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到贵州六盘水,住一晚,次日清晨再转搭6小时大巴。我熟悉那条线路上每一个上坡、下坡、拐弯、村庄、车站、河流、山峰、隧道、桥梁、城市的轮廓,还有很多气味。我记得韶关站月台上煲仔饭的气味(5块一份,奉送砂煲一个);我记得餐车的贵价小炒的气味(那时吃不起);我记得乘务员推着小车、走第一遍卖25走第二遍卖15走第三遍卖10块但已经凉了的盒饭的味道……
那年夏天,南方水灾,广西段铁路运输中断。我困守广州,每天坐在宿舍走廊,用一个搪瓷饭盆,生吃三年的老火腿。终于熬到可以走,却在广州火车站丢了钱包。身份证随钱包而去,我揣着另一个裤兜里藏的50块钱,提着两袋「华丰」方便面,踏上回家路途。华丰面只卖7毛,当年在学生群体中是一种普遍的补餐食品。油炸面,不健康,但既可以泡着吃,也可以嚼着吃,廉价地满足油水不够的肠胃。
靠这两袋方便面,以及腆着脸向邻座蹭来的半个苹果、几个橘子,熬过42个小时没有空调的拥挤硬座(两人位上坐了四人!),终于在第三天傍晚到达六盘水站。
六盘水是周边货运枢纽,客运就乏善可陈。火车站附近,有大量家庭旅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房价,四人间只要5块,所谓「单间」,也只要12块。卫生间当然是公共的,洗澡根本就只能去外面的澡堂子。曾经和耍猴的同住一室,人在床上呼呼大睡,那猴就拴在木头床脚哀哀低呼。
问了三个揽客的,总算有一家肯接受免身份证入住。花12块住了单间,再去汽车站买张35块的次日长途车票,坐在家庭旅馆堂屋的破旧沙发上,我想,再饿上一顿两顿,也算不得什么。
当天的晚饭出其不意地得到解决。几位来自矿区的学生,到六盘水取领高考成绩,和我住同一旅馆。聊了几句,也颇投缘,就叫我一起吃饭。除了寻常炒菜,居然还有一整只鸡!那是学生们难得的奢侈告别宴——待领了成绩,他们就快各奔东西,而我这个蹭饭的,也将成为他们人生旅途上小小插曲。次日,我怀揣最后2块钱去搭长途大巴,没有道别,却是满心感激。那只鸡的样貌与味道,也铭刻在生命中那个普通又特别的日子,以至于后来没有任何一只鸡,可以与之媲美。
还有一次,从昆明去广州,卧铺。无眠,坐望黑漆漆的窗外。隔床老头也睡不着,用搪瓷缸装了卤猪脚,又从挎包里摸出一瓶散装白酒,邀我同饮。老头不懂普通话,我也不明白他说的方言。一老一少,沉默相对两个小时,就着车轮压过铁轨缝隙的「况且」声,吃完卤猪脚,一人一口喝完那瓶酒,各自回铺睡去。次日起来,老头与他老伴,已在途中下车。我与他们再无交集,可直至如今,好像还闻得到卤猪脚的药材香,和散装酒强烈如刀子的口感。
绿皮车已有10年没有坐过,但有关绿皮车上吃的记忆,还有好多可写。吃,首为果腹,次为享受,再往上去,无非与人、事相应,将一些好吃或不好吃的味道烙在记忆中,作一生的嚼裹。
文 韩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