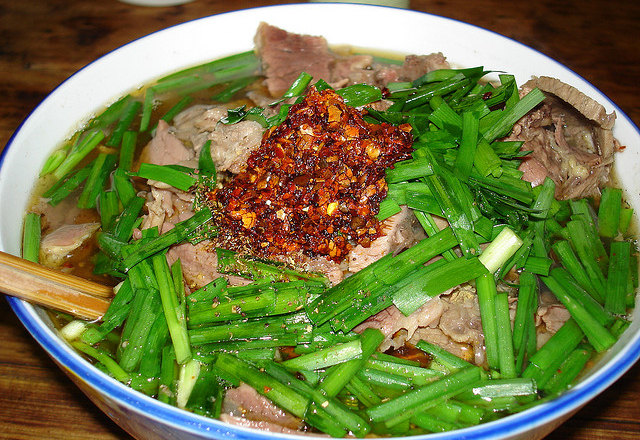看二毛的《妈妈的柴火灶》,抹上渣海椒放在火钳上烤的大锅巴把我给看美了,二毛写美食,总是能让人咂摸出不少东西,就像现在,我忽然就想起了小时候爷爷家用柴火灶和大铁锅蒸出来的热腾腾的大馒头。当时蒸馒头之前大娘总要问我想不想吃烤馒头,如果想,她就会在往竹屉上摆馒头时把馒头离铁锅稍近点儿,这样等馒头蒸出来,离铁锅边儿最近的那几个馒头,表皮总是金黄酥脆的,还带着一股特有的焦香,是如今超市里买的加了各种调味料和油脂的烤馒头片所不能比拟的。如此想来,倒是和二毛所心心念念的锅巴如出一辙,只是一个是北方的面点一个是南方的米食罢了,都是柴火灶和大铁锅成就的美味,都蕴含着家庭主妇们平凡生活中的大智慧。
为了节省能源,也图个省事,小时候每次蒸馒头都是满满的一大屉。一掀锅盖儿,热腾腾的蒸汽把视线挡了个严严实实,等到白气稍散,一个个敦实可爱的大馒头才肯露出本来面目。农村自家做的馒头和现在城里馒头店卖的馒头不太一样,这种不同首先就体现在个头上,自家做的馒头个儿头很大,能顶两三个甚至三四个外卖的馒头。北方人,尤其是北方的农村人食量很大,一顿饭要提供在地里劳动半天所需的能量,再加上每顿饭菜少油轻不经饿,所以一顿饭两三个馒头下肚没有问题。这种馒头往往是用老面发酵的,也就是把上次做馒头时发酵的面团留下一块儿,在下次做馒头时作菌种用,我们老家把这种面团叫做面酵。用面酵做的馒头成色不像外卖馒头那么白,略带麦色,却更显得朴实、家常。老面里有很多的乳酸菌,所以用老面发酵做的馒头会有一股独特的酸味儿,有的人会拿碱去中和,不过我却很是偏爱这种独特而质朴的味道。
当时没有冰箱,老面又极难保存,所以怎样使面团不腐坏也是个大问题,关于这点,我一直没弄明白,不过巧手的家庭主妇自有其智慧,大娘每次做馒头都会留下一些面团放在面袋子里,有个很形象的说法叫喂面酵,和西方老式面包喂酵母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因为馒头是每顿饭的必需品,再加上当时人们食量都不小,所以隔个几天就要蒸次馒头,面酵也不至于放坏,即使坏了也没关系,左邻右舍往往家家面袋子里都有着这么一块儿面酵喂着,借来用用,等做完馒头再留下一块儿新面酵还回去就行了。
现在人们的主食越来越丰富,再加上生活节奏加快,自家蒸馒头的次数越来越少,而面酵的难得以及面粉与碱面比例的难以掌控更使得老面馒头逐渐淡出了普通人家的厨房,想吃馒头了,去馒头店或者超市买上一两斤就行,还有的直接去超市买那种速冻的馒头,只是加了过多泡打粉和白糖甚至奶油的馒头,早就没了馒头味儿了。妈妈是老师,每年都有固定的寒暑假,每次放假,妈妈总要去楼下烧饼摊子上买上一块儿发酵好的面团做上一锅老面馒头,还是一如既往的劲道、有嚼头,只是少了柴火灶和那口大铁锅,想吃原汁原味嘎嘣脆的烤馒头是没机会了。
家里有亲戚开着一家做馒头的小作坊,每年都会送一大袋子老面馒头到我家,妈妈总是把它们冻在冰箱下层,想吃的时候拿几个出来,解冻以后上锅蒸。这种传统作坊做出来的馒头极好吃,比小时候吃到的馒头个头小巧很多,也精致很多,颜色也要白一些。因为加了碱面,面酵的酸味儿被去掉了,小麦粉的清甜味倒得以彰显出来。这种馒头有着北方人一样的实在,暄软,但不软趴趴,吃的时候甚至还能一层层揭着吃,一看就是下了苦功夫的。这才是真正能作为主食的馒头。
来到千里之外的广州读大学,口味也被迫做出一些改变。拿馒头来说,广式馒头是以点心的身份出现的,以暄软、清甜著称,里面加了大量的牛奶和白砂糖,小小的个头,一捏就更是小得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的馒头确实只能作为点心,不能成为扛饿配菜的主食。倒是偶然间在清真食堂吃到的刀切馒头让我大为惊喜,结实、淡淡的麦色、层次分明、独特的面香,很有嚼头,满足!
据说面食比米更能养胃,这也是有一定的依据的。面和米有着不同的淀粉结构,相对而言,面食更易消化,因此胃酸分泌偏少,使胃不致于过度疲劳。小麦性甘,味平,能养心气,中药里有个“淮小麦”,专门用来养心安神。面条里含碱,再加上煮过的面条软和易嚼,其养胃功效更是为世人所熟知。在我们老家还有个养胃的土方,就是把馒头切片晒干,可以做主食,也可以没事儿当零食吃,每次吃了不消化的东西,我都会晒上几个馒头片吃。
同样是馒头,在上海却是不一样的东西,上海的南翔馒头店远近闻名,甚至还开到了韩国、日本、新加坡,但你在它家绝对找不到传统意义上可以被称为馒头的东西,这是因为上海人所说的馒头,正是当地著名的小笼包,皮薄馅大,汁多味鲜。这也引起了很多人对馒头究竟该不该有馅儿的争议,查了资料才知道,馒头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宋朝高承的《事物纪原·酒醴饮食·馒头》里记载,“稗官小说云:诸葛武侯之征孟获,人曰:‘蛮地多邪术,须祷於神,假阴兵一以助之。然蛮俗必杀人,以其首祭之,神则向之,为出兵也。’武侯不从,因杂用羊豕之肉,而包之以麪,象人头,以祠。神亦向焉,而为出兵。后人由此为馒头。”动画片《中华小当家》里有一集正是馒头之间的对决,讲到了馒头的起源,面点王罗根还做出了当年的镇魂馒头。如此可见,因谐音“蛮头”而得名的馒头,其祖上或许真的是有馅儿的。不过历史归历史,我们怀念的,往往就是我们从小所熟知的东西罢了。
作为土生土长的中原人,我们是顿顿离不开馒头的,早上稀米汤或者玉米面粥配馒头,中午馒头配炒菜,晚上即使吃面条也要备上几个馒头当嚼头儿。小时候家里条件不怎么好,零食也多和馒头有关,用筷子一插,架在煤球炉上烤烤就成了烤馒头;馒头中心挖个洞,里面倒点白砂糖或者撒点盐、浇几滴香油就能蘸着吃了;馒头切片,在调制好的酱油醋水里浸泡一下下锅炸,出锅后撒点孜然粉,就成了香喷喷的炸馒头片啦。每日与馒头相伴,使得我每次看到街上的馒头店都有一种家的感觉,尤其是在有着微微凉意的早晨,蒸笼盖一掀,满满的热气腾地一下升起,白胖的大馒头在蒸汽里若隐若现,散发着诱人的麦香,此情此景,总能把人心都给看化了。
对于背井离乡的北方游子来说,唯这一屉热腾腾大馒头,最难将息!
文 丫米的小确幸
图 Quan Shen on Flickr 循CC协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