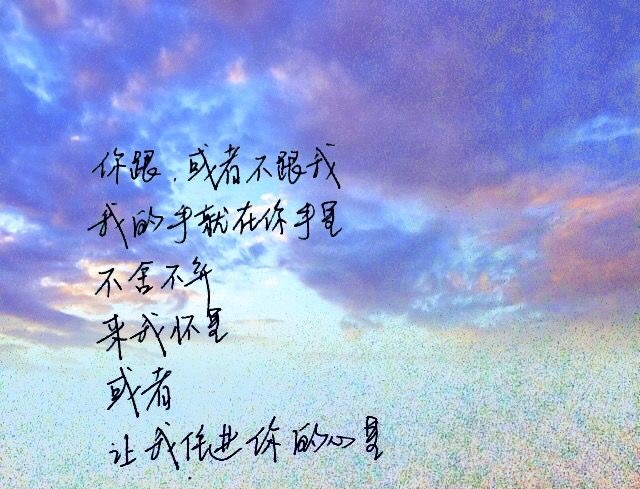小时候对于吃的记忆,或者更具体地说是对于“好吃的”的记忆,全部来自于爸爸。
妈妈是个懒散的人,从不肯好好学做饭,除了西红柿炒鸡蛋,鸡蛋炒西红柿以外什么都不会做。好在我小时候好养活,给啥吃啥,倒也没因为挑食等臭毛病而饿成一道闪电。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爸爸偶尔也会下厨露几手,于是,“爸爸菜”就成了我儿时最期盼的味道。
父母离异前记忆最深刻的应该就是“樱桃肉”了,应该跟现在北京有些餐馆不伦不类的糖醋里脊有些类似,不过菜品形状从条状变成了粒状。小时候运气好赶上爸爸妈妈心情都不错,爸爸就会塞给我一点钱,多少钱不记得了,让我去街对面的小食杂铺子买一罐番茄酱,顺便还能给自己买两颗“小淘气”糖,屁颠儿屁颠儿抱着番茄酱跑回家,就巴巴抱着爸爸大腿等着他经典拿手的“樱桃肉”。那时还小,不记得具体的操作步骤了,后来也问过爸爸做法,就是把里脊肉切成大拇指大小的小方丁,裹上淀粉下油锅炸,炸两到三遍,再在锅里下番茄酱、糖、醋、盐、水淀粉,最后放进肉,等到肉都挂满浆,出锅,完活。
印象中每次这份红彤彤、油亮亮、酸酸甜甜的樱桃肉端上桌以后我都会笑眯眯地一口接一口,好像不会用筷子也没关系,烫手烫嘴也没关系,管他形象不形象呢,天生吃货加女汉子,谁都别拦我。而这个时候的爸爸妈妈也都会一边说别急别急,慢慢吃慢慢吃,小心别烫着小心别烫着,一边不停往我碗里夹肉。
儿时难得的关于“家”的温馨画面因为一盘“樱桃肉”而让人缅怀。
好像小时候爸爸会做的菜有好多,有好些都带些“传奇”色彩。印象深刻的有一道“泥鳅钻豆腐”,就是冷水下锅放进活泥鳅和卤水豆腐,小火慢慢加温,在加热的过程中,泥鳅会因为受不住水温而钻到相对凉快的豆腐里面去,等最后出锅的时候只见豆腐不见泥鳅,汤鲜味美,豆腐和泥鳅香滑顺口。当然,这是我爹跟我说的,小时候我因为觉得泥鳅很“可爱”而不敢吃,就只能喝点汤吃点咸菜,至于味道,完全没印象,相对于现在来说应该算是一种遗憾了吧。
初中升高中那年爷爷奶奶出国送妹妹去她父母身边,家里就又剩我和老爹俩人相依为命,说是相依为命,可在吃上,我那同样吃货的老爹可真没亏待我一点。头一星期,正正一周,我爹给我做饭愣是没有重样儿过。家常的包子饺子、卷饼盒子、刀削面打卤面。新奇的荷叶鸡、啤酒鸭、水晶肘子。火锅烧烤不能少。当然了,餐桌上永远不会出现西红柿炒鸡蛋。
后来爷爷奶奶回国那天我和爸爸大吵了一架,也就从那以后我和爸爸好像越来越远,很多很多年我都没再吃过爸爸做的饭,直到大学第一年暑假回家,爸爸说给我做饭吃,我才再一次吃上了“爸爸的味道”,可惜的是,不知是我的嘴巴变刁了还是爸爸真的好多年不做饭了,那一顿的味道再也没有儿时的记忆,却只有少小离家和感叹时光催人老的哀伤。
现在的我也算是继承了老爸的“大厨”天赋,做出来的饭菜也算“可口美味”,也不枉当年大吃货对小吃货的一片爱意。
只希望时光啊你慢点走,不要让爸爸妈妈的两鬓染上风雪,也可以让我多做些美味佳肴和他们共享天伦。
文/Kitty
图/Alexandra Moss 循CC协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