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堂里恼人的老口蛋黄
作为一个小电锅被宿管阿姨收走两次、至今不敢要回来的倒霉孩子,如果早上想补充点蛋白质,我不得不屈服于学校食堂的白煮蛋。
可它是多么令人绝望呀:
 蠢笨的个头,莫名坚硬且难剥的外壳,坚韧弹牙如皮蛋,蛋白竟然还自带分层。更不用说外层发青、内里掉渣,口感令人联想到粉笔的老口蛋黄……
蠢笨的个头,莫名坚硬且难剥的外壳,坚韧弹牙如皮蛋,蛋白竟然还自带分层。更不用说外层发青、内里掉渣,口感令人联想到粉笔的老口蛋黄……
若是早餐时段销量不佳,午餐你还可以在炒菜中见到它的身影,只是想到都忍不住在齿间蹦出个脏话来。
 想打打牙祭的话,我会跑去市里的轻食店,叫份班尼迪克蛋沙拉。可层层蔬菜上窝着的那颗漂亮的水波蛋,往往又因为从厨房到餐桌这短短几分钟的冷却,透出点腥气。不由得让人暗暗觉得,这花出去的几十大洋有些划不来。
想打打牙祭的话,我会跑去市里的轻食店,叫份班尼迪克蛋沙拉。可层层蔬菜上窝着的那颗漂亮的水波蛋,往往又因为从厨房到餐桌这短短几分钟的冷却,透出点腥气。不由得让人暗暗觉得,这花出去的几十大洋有些划不来。

有时也会苦恼,到底是我太过挑剔,还是鸡蛋这家伙真的太难料理,吃到一颗称心如意的蛋太难太难。
难寻一颗完美的鸡蛋
有次去女友家捣乱,看她熟练地掌勺做起“番茄炖牛腩”这种大菜,而我呢?只能像个纨绔子弟,倚着门框说些逗趣的漂亮话,装模作样地指点两下。我幽怨地感叹:“鸡蛋基本可以代表我荤菜料理的最高水平……”

这话虽然听来好笑,但仔细想想,鸡蛋可谓是最有性格的食材,会煮蛋已经是件让人得意的事了。
它可以朴素到每家每户的一餐一饭,也可以一转身,登上最高级餐厅的餐桌,它几乎可以搭配任何的食材,又不至于抢走它们的风头;也可以单独在料理中,大大方方地展现出自己美好的味道……这么看来,它俨然有些大家闺秀的风度不是吗?
我曾煮过一颗完美的水波蛋
直到如今,我还是妈妈眼里的厨房恐怖分子,可作为一个吃货,哪里放得下爸爸刚从老家带回来的笨鸡蛋?在心里天人交战许久,终于食欲熏心,下定决心违抗老妈“不许下厨”的圣旨。
不管三七二十一,我迅速地接水、大火煮沸、放蛋、小火微焖,也不知道具体煮了多久,心里默念一声“成了!”便关火、移锅、轻轻用凉水一激……
 迎着迅速冷却带来的白汽,我迫不及待地把蛋捞出,用餐刀小心翼翼在半腰磕出一圈缝,双手捏住两端,然后轻柔地豁开缝隙——一汪水波蛋跃然眼前!
迎着迅速冷却带来的白汽,我迫不及待地把蛋捞出,用餐刀小心翼翼在半腰磕出一圈缝,双手捏住两端,然后轻柔地豁开缝隙——一汪水波蛋跃然眼前!
用刀划开蛋白,犹如木桨破开水面,蛋黄不慌不忙地流出来……凑上去轻啜一口,蛋的鲜甜在舌尖爆炸,那感觉仿佛触电一般,在脑中噼里啪啦放起漫天烟花……
原来,这就是完美水波蛋的秘诀
我喜欢的美食家蔡澜曾率领团队探访保罗·博古斯,这位米其林三星大厨对一枚鸡蛋也有自己的见解——“每个人都有自己对事物的癖好,鸡蛋要几成熟,都应由吃的人做决定,要做到他认为最完美的鸡蛋,只能亲自来做。”

“而煮出一个随心所欲的蛋其实最难,一个懂得食物真味的人,是从自由的思想和个体的尊重出发的。”
是啊,越是简单的食材,越是蕴含无穷的变化。而味觉又是那样主观的东西,评判一颗鸡蛋是否“完美”,要动用的除了舌头,大概,还有心。
后来,我也曾尝试复制那天的水波蛋,可似乎再也找不到那个味道。
是哪里不一样了?
我想,大概就是那份“随心所欲”使然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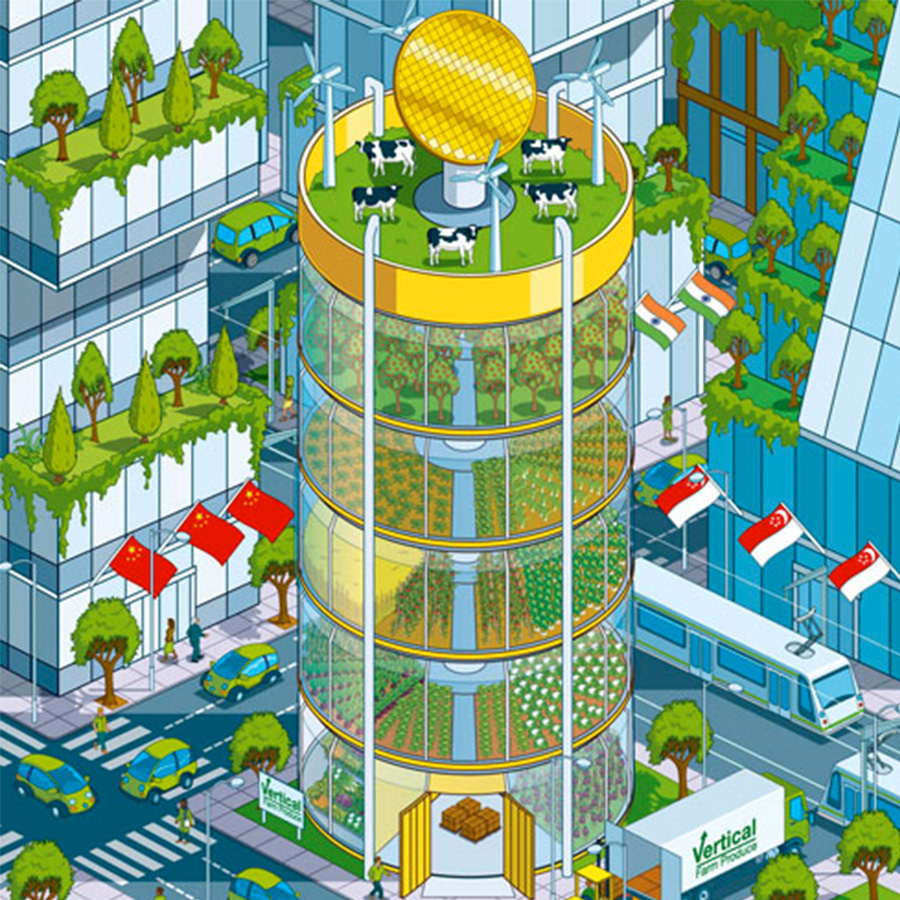



 小时候,外公每半年要去县里领一次养老金,那是我最期待盼望的旅程——县里有美味的豆皮小店。陈旧的长途汽车颠簸得难受,可想到马上就可以吃上一碗新鲜出炉的豆皮,任何不适都烟消云散了。
小时候,外公每半年要去县里领一次养老金,那是我最期待盼望的旅程——县里有美味的豆皮小店。陈旧的长途汽车颠簸得难受,可想到马上就可以吃上一碗新鲜出炉的豆皮,任何不适都烟消云散了。 我最爱坐在小店塑料椅上,伸长了脖子,看师傅做豆皮。老师傅将用绿豆、大米磨成的面浆往大锅浇上一圈,有泼墨一般的写意。手里握着三两个鸡蛋,单手逐一磕破,手腕轻轻抖动,鸡蛋就被利索地打进锅里了。握着锅边,慢慢地转动让豆皮受热均匀。之后,铺上自家蒸制的醇香糯米,撒上卤制的小豆干和葱花。
我最爱坐在小店塑料椅上,伸长了脖子,看师傅做豆皮。老师傅将用绿豆、大米磨成的面浆往大锅浇上一圈,有泼墨一般的写意。手里握着三两个鸡蛋,单手逐一磕破,手腕轻轻抖动,鸡蛋就被利索地打进锅里了。握着锅边,慢慢地转动让豆皮受热均匀。之后,铺上自家蒸制的醇香糯米,撒上卤制的小豆干和葱花。

 我正走在去上环九记牛腩的路上。转入歌赋街,两层的小楼外和传说一样排着长队。有人说这里曾有无数明星光顾,但我探寻到来,只为了那个从青春年少一直仰慕至今的男人——张国荣。
我正走在去上环九记牛腩的路上。转入歌赋街,两层的小楼外和传说一样排着长队。有人说这里曾有无数明星光顾,但我探寻到来,只为了那个从青春年少一直仰慕至今的男人——张国荣。 高三的那个冬天傍晚,穿过操场,来送饭的妈妈向我招手。看着她热切的目光,想起月考成绩的不如人意,愧疚、难过和自责在心头百味杂陈。
高三的那个冬天傍晚,穿过操场,来送饭的妈妈向我招手。看着她热切的目光,想起月考成绩的不如人意,愧疚、难过和自责在心头百味杂陈。 从未亲眼目睹你的风华绝代,也没在你如日中天的时候热力追捧。
从未亲眼目睹你的风华绝代,也没在你如日中天的时候热力追捧。 而如今,这一碗牛腩伊面,希望还是你曾经喜欢的那种味道!
而如今,这一碗牛腩伊面,希望还是你曾经喜欢的那种味道!
 麻辣土豆片自然以麻和辣出名,吃时麻辣鲜香的酱汁围着舌头打了个转儿,像是用针在扎舌尖一般。那肆意的辣味,扎得人鲜血直流,可还忍不住嚷嚷:“使劲扎!使劲扎!”如果说紫薇被容嬷嬷扎针是因为皇后的视她如眼中钉的话,麻辣土豆片的扎针酷刑是你心甘情愿的——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麻辣土豆片自然以麻和辣出名,吃时麻辣鲜香的酱汁围着舌头打了个转儿,像是用针在扎舌尖一般。那肆意的辣味,扎得人鲜血直流,可还忍不住嚷嚷:“使劲扎!使劲扎!”如果说紫薇被容嬷嬷扎针是因为皇后的视她如眼中钉的话,麻辣土豆片的扎针酷刑是你心甘情愿的——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而冬天的时候,吃麻辣土豆片最过瘾,门外北风嘶嘶,盘中却是热火朝天,所有的快意恩仇都凝在了一盘麻辣土豆片里,成为治愈伤口的最佳良药。
而冬天的时候,吃麻辣土豆片最过瘾,门外北风嘶嘶,盘中却是热火朝天,所有的快意恩仇都凝在了一盘麻辣土豆片里,成为治愈伤口的最佳良药。 吃着吃着,忽然觉得,麻辣土豆片不就像爱情一样吗?
吃着吃着,忽然觉得,麻辣土豆片不就像爱情一样吗? 越是讨厌一个人,便越要纠缠你;明明那么喜欢,却似乎感觉不到你的好;明明答应要娶你,转眼之间却另娶他人;明明那么在乎,而你还是喜欢那个令你伤心的男人。
越是讨厌一个人,便越要纠缠你;明明那么喜欢,却似乎感觉不到你的好;明明答应要娶你,转眼之间却另娶他人;明明那么在乎,而你还是喜欢那个令你伤心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