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吃过排骨年糕吗?
要是你到南方来,就会知道,年糕不是一种过年才吃的应景食物,而是种非常普遍的基本食材。早上有糖年糕,泡饭年糕,中午有黄芽菜炒年糕,晚上有毛蟹年糕,排骨年糕。
软软糯糯的,有点绵,有点嚼劲,片状的,条状的,它们不是点缀或者配菜,而是饭桌上正经的主食成员。一说到主食,亲切的,接近黄土地的朴实的自然清纯感简直是扑面而来。
基本的营养元素,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烟酸、钙、磷、钾、镁,和满满的饱腹感足够很好地维系生命的动力。而祖祖辈辈都不是农民的我,不知怎的,对于黄土地,有种融合了敬畏、感恩和亲近的未名情愫。看《舌尖》系列里顶着黄沙做黄馍馍的农民有种幸福、感动、敬畏交杂之情。比看一个包包可有感情多了。
我们家吃年糕的传统是不会做饭的妈妈建立起来的。妈妈可以一星期吃上3天年糕也不烦。(我曾经怀疑她就是奥特曼故事里那个奇奇怪怪的年糕怪,专门降临来扫荡地球上的年糕。)没什么菜色够得上我妈妈带饭标准的日子,她对我爸说,黄芽菜炒年糕吧。
新鲜的黄芽菜跐溜下锅,淋上老抽,2分钟之后下条状的被切成片状的宁波年糕,起锅前再倒入一点儿生抽,一款菜和主食合一的轻量级正餐美食就完成了。而毛蟹年糕则需等待时日,非得九雌十雄的季节才能成就这款地位相当平民大餐的晚餐美食。

排骨年糕,比黄芽菜年糕正式些,比毛蟹年糕日常些,刚好是中间的家常,对我来说最对味。
我爸烧菜,是小清新中的重口味,重口味中的小清新。罕见用大料,调味却不寡淡,绝不会出现吃了几口需要另外找酱菜就着吃完的事。这款排骨年糕,我认为是我爸的代表作之一,有菜的足料滋味,也不失年糕的本味,让排骨成为主角,让年糕有戏可唱,在一口浓郁饕餮后,有淳朴粘稠香。
制作法则和黄芽菜可说是一脉相承。秘诀一是原材一定要好,大排必须是菜场购买的新鲜料,不是速冻的陈肉,年糕的软硬程度适中,以产地宁波的为上佳。秘诀二嘛,则是从容的心情。是的,说起来有点玄乎,其实却是真切的实话。下锅不急不躁,倒酱油既不胡乱一冲手抖下去霍乱食材,也不过于小心斟酌畏首畏尾误了时辰叫年糕粘锅外貌不美丽。
所以说我一直觉得,烧得好菜的人,如果不是厨师做职业,必定是非常热爱生活的,且是能热爱平淡生活的。那葱油酱料,油烟飘忽,哪里是一盘热腾腾的菜呢,是热腾腾的有温度的生活本身吧。
同一屋檐下的我妈,则是水煮蛋煮6个会破5个的主,和技能无关,和态度有关。锅里煮着呢,她便忙不迭得去客厅看电视,总得锅仰马翻才来收拾残局,慨叹一下,太麻烦了。当然,这只是不同而已,每个人人有权选择怎样过日子,我妈这款的不也有老天给配置我爸这款的老公嘛。
离开了上学的日子,好像时间是一年甚至几年这样过的,再也不是一天天的,一家人在一块儿吃饭也已经算是难得温馨,像读书时那样期待一顿早就规划好的精致美食很少很少了。爸味排骨年糕的美好,渐渐成为脑海里的一抹浓香入味。
然而,我没有换一座城市生活,大街上不会缺少爆款排骨年糕。所以,即使是刻意拒绝,也终有一天,狭路相逢。
 和同事在等饭吃的老上海馆子吃上了上过美食节目的爆款排骨年糕那天,也颇有记忆点。年糕是炸的,排骨也是炸的,年糕上淋上的是甜甜的酱油汁,趁热马上吃,一咬是酥脆可口,非常不错的好点心的应有之义一样不缺。有甜,有咸,有香,有脆。大块的炸猪排呢,勾芡过几层,咬起来是意料之外的鲜嫩。同事吃得大为满足,赞不绝口,我呢,也觉得是不错的点心。可是就是先有了爸味排骨年糕打底,总觉得那浓油赤酱的做法,才是真味,饭菜融合的巧思,而煎炸之物,实在太像鸡排之类的需要配奶茶的下午小食。
和同事在等饭吃的老上海馆子吃上了上过美食节目的爆款排骨年糕那天,也颇有记忆点。年糕是炸的,排骨也是炸的,年糕上淋上的是甜甜的酱油汁,趁热马上吃,一咬是酥脆可口,非常不错的好点心的应有之义一样不缺。有甜,有咸,有香,有脆。大块的炸猪排呢,勾芡过几层,咬起来是意料之外的鲜嫩。同事吃得大为满足,赞不绝口,我呢,也觉得是不错的点心。可是就是先有了爸味排骨年糕打底,总觉得那浓油赤酱的做法,才是真味,饭菜融合的巧思,而煎炸之物,实在太像鸡排之类的需要配奶茶的下午小食。
我明白的,快捷,便利,好复制的美食已是不易。而且随处可得,至多不过排队等一会儿罢了。这样的吃食已经足够安抚僵直了一整天的背脊脖颈,让胃得以安心慰藉,让脑袋放空一下,就是凡俗庸常一天的奢侈。
有人说,生命是从A到B的直线,有些人选择绕路到C,另一些人选择绕路到D,然后在结尾处归于B,这就是命运。这样说,从幼时的有大把时间可以享受时间的本身,到略长大的可以单任务地专注于一件事务,到长大之后得每天多任务地为了生活做这做那而心平气和,可能本来就是命定的路线。童年的幻想乐园封存了,真实的日常进行着,不管未来能不能过着理想状态里的生活在别处,都要乐观、积极地安享当下。也许是只此一趟的生命旅程的奥义。
排骨年糕不需要PK,而生活,当然也不需要。
图文 By 心念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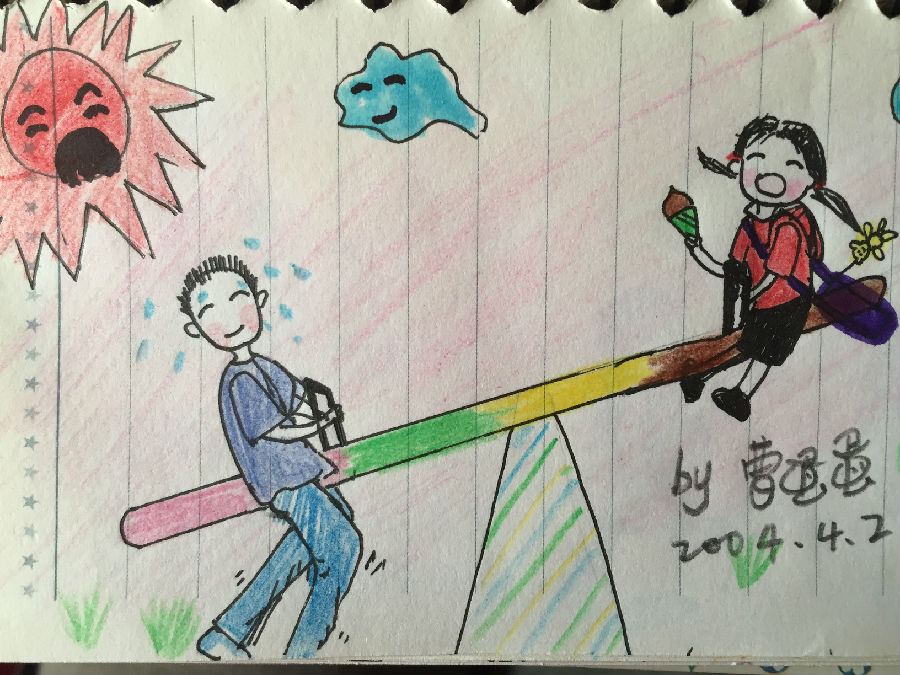 上了大学,爱上了一款蛋筒冰淇淋,叫可爱多,3块5一支,各种口味的,蛋筒底部还藏有一整块巧克力的福利,冰淇淋、巧克力,连同蛋筒一起吃掉,就感觉拥有了全世界的甜蜜。当然,也是因为送我第一个可爱多的人,是我喜欢的人。四年里,他为我买了很多可爱多,也把永远说成了一颗糖,直到后来的后来,我一个人站在夜色中的北京天桥上,捧着一支蓝莓味儿的可爱多,在寒风中大颗大颗的掉着眼泪的时候,感觉未来停止了,整个人生也许就这样完蛋了。我想起他曾经惹我生气,跑去麦当劳一口气吞掉三个冰淇淋,哄我开心的傻样子……那个人就这样被冰冻在可爱多里了。
上了大学,爱上了一款蛋筒冰淇淋,叫可爱多,3块5一支,各种口味的,蛋筒底部还藏有一整块巧克力的福利,冰淇淋、巧克力,连同蛋筒一起吃掉,就感觉拥有了全世界的甜蜜。当然,也是因为送我第一个可爱多的人,是我喜欢的人。四年里,他为我买了很多可爱多,也把永远说成了一颗糖,直到后来的后来,我一个人站在夜色中的北京天桥上,捧着一支蓝莓味儿的可爱多,在寒风中大颗大颗的掉着眼泪的时候,感觉未来停止了,整个人生也许就这样完蛋了。我想起他曾经惹我生气,跑去麦当劳一口气吞掉三个冰淇淋,哄我开心的傻样子……那个人就这样被冰冻在可爱多里了。 我遇到了新的冰淇淋DQ,我用自己的小名重新给两个字母定义为DANDAN QUEEN,并乐此不疲的跟别人嘚瑟,恨不能拿到代言。爱上了抹茶的口味,开心不开心的时候都会去吃一杯,心情瞬间就能冷却下来,能想通很多,也能消化很多,人生里有这样的解忧之物,好像也不是很难过了。我开始相信,总是有些人会大器晚成,也总有一些爱会姗姗来迟,我们唯一能主宰的命运只有清空杂念,坚守自己。
我遇到了新的冰淇淋DQ,我用自己的小名重新给两个字母定义为DANDAN QUEEN,并乐此不疲的跟别人嘚瑟,恨不能拿到代言。爱上了抹茶的口味,开心不开心的时候都会去吃一杯,心情瞬间就能冷却下来,能想通很多,也能消化很多,人生里有这样的解忧之物,好像也不是很难过了。我开始相信,总是有些人会大器晚成,也总有一些爱会姗姗来迟,我们唯一能主宰的命运只有清空杂念,坚守自己。 淡淡缭绕的雾气,让我想起来很多年前,当我还是孩子。北方寒冬的农村,父母在北京工作忙,往往会在寒暑假把小孩放到各自长辈家,没错,我的姥姥姥爷家在河北;我并不是很喜欢那里,一个字,冷。回去之后,我是极其不愿出屋子的,因为当时农村烧炕,没暖气,没有自来水,需要从水缸舀水,而屋外的空气和景色,都透着一种清冷。冬季的华北大地,萧瑟、白蒙蒙一片、光秃秃的土地,着实没的玩,没的看。在小孩子心里,这两点恐怕最重要。
淡淡缭绕的雾气,让我想起来很多年前,当我还是孩子。北方寒冬的农村,父母在北京工作忙,往往会在寒暑假把小孩放到各自长辈家,没错,我的姥姥姥爷家在河北;我并不是很喜欢那里,一个字,冷。回去之后,我是极其不愿出屋子的,因为当时农村烧炕,没暖气,没有自来水,需要从水缸舀水,而屋外的空气和景色,都透着一种清冷。冬季的华北大地,萧瑟、白蒙蒙一片、光秃秃的土地,着实没的玩,没的看。在小孩子心里,这两点恐怕最重要。 我对豆腐花的记忆起源于幼时。那时,每逢周末我和表弟们都会到旧城外婆家里玩。小孩子起来得早,早餐也吃得早 ,中午饭又迟。外婆大概是怕我们饿,早上买完菜就会到小摊上买上几袋豆腐花回家。
我对豆腐花的记忆起源于幼时。那时,每逢周末我和表弟们都会到旧城外婆家里玩。小孩子起来得早,早餐也吃得早 ,中午饭又迟。外婆大概是怕我们饿,早上买完菜就会到小摊上买上几袋豆腐花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