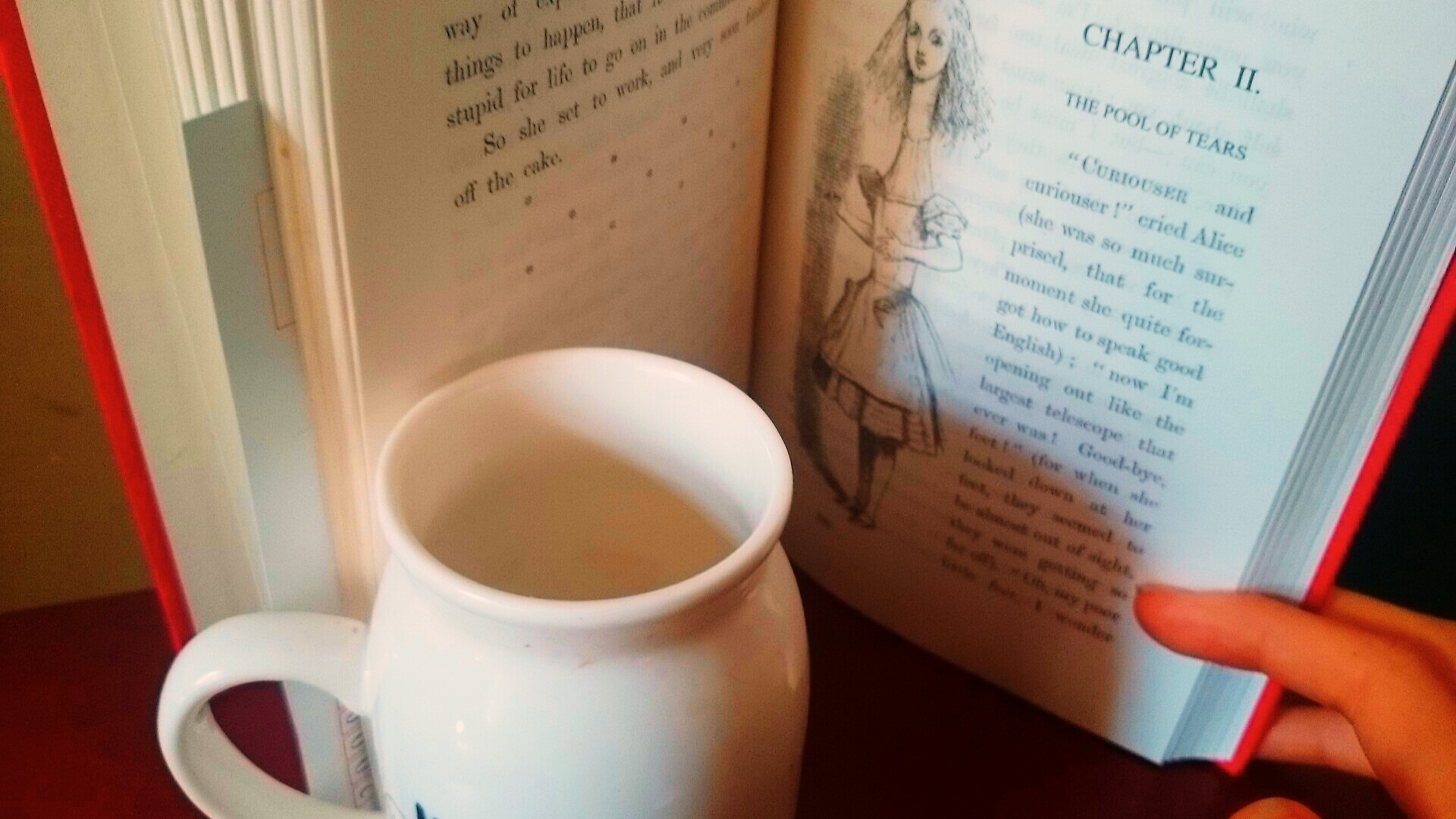大家都说番茄炒蛋是一个很普通的家常菜,可是我不这样认为。我曾经不挑场合郑重其事地向人们宣称过我的番茄炒蛋是祖传技法,多次让谈话气氛顿生尴尬。
事实上,在13岁那年父亲教我做番茄炒蛋的时候,他的面容也是一样的郑重。我总不是太能领会父子间的一些微妙感情的传递,但是细致地观察和完美的学习,还是能做到的。
后来,我在人生中第一次独自去单身姑娘家的时候,就给她做了这道菜。
原料的选择上来说并无特别,番茄只需要选择大个深红的即可;鸡蛋更是随遇而安——毕竟寻常人家的备菜远达不到《随园食单》中当朝才子深宅大院里的精挑细选。
但是对于番茄的处理上则稍显复杂。番茄洗净,用开水仔细烫过,慢慢剥下外皮,横切开来,用小勺挖去内籽,剩下的果肉才是真正使用的,切成小碎块。
奶奶在世时曾经跟我聊过这种番茄的处理方法,大致说的是保留了七八十年前国人处理“恶魔之果”的谨慎态度;后来我却在PASTA典籍中读到,意大利人制作红酱意面时对番茄处理有惊人的相似。
当然番茄炒蛋这味菜式不可能需要牛油或者蒜碎。我要做的,首先是铁锅烧热,倒入花生油,油未开时便加入整个菜式的盐量。待油稍热,葱花爆锅,倒入番茄碎块,翻炒闷煮。
番茄煮20分钟析出蕃茄红素已经是众人皆知的秘密。但是这一道番茄炒蛋的番茄平均要煮30-40分钟。而且全程不加水,完全靠小火慢炖并适当翻炒。
番茄差不多的时候才可准备鸡蛋。数量上来说,我恪守的是“多少个番茄配多少个鸡蛋”的原则。煮番茄的同时,另取一锅开一灶头,锅干放油,待油温稍高于煎蛋的温度——此时才可以快速将蛋液打散——温度稍一合适便冲下蛋液。鸡蛋不能加盐。
说是炒蛋,其实更像是煎蛋做法,控制火候让整个蛋面因油温膨胀松软而又不至于烤上焦边。此时将煮好的番茄汁倒入,快速搅拌并用铲子插碎原本完整的蛋面(并给菜式带来一点随意感)。这样,在上桌的时候因蛋的温度下降而收缩时,将会吸满浓厚番茄汁,成为天衣无缝的番茄鸡蛋搭配。
还有最后的关键一步。关火之后撒上细切的香菜碎,让整个菜式发生奇妙的味觉升华。
这道菜端上桌之后,姑娘发出了赞叹:“做的好像我妈妈做的啊!”我承认,那时听到这句非常受用。
几年后,我斜靠在厨房独自凝视翻腾的番茄汁的时候,才突然恍然大悟,原来那句只是放之四海皆准的恭维套话。万幸的是,套话只用来说给生命中的过客。
后来,我去过许多姑娘的家,也在自己家里招待过很多朋友,都间或默默地做过这道番茄炒蛋,只是不再提过这道菜的特别。有朋友曾经好奇菜式的怪状以及味道的特别故而发问,于是有了前面我唤醒尴尬气氛的回答。
再后来,我终于建立了自己的家庭。某一天,我为妻子准备她最爱吃的白切鸡的时候,妻子靠在我的肩膀上喃喃细语:“刚认识你的时候你说你会做番茄炒蛋,我以为你不会烧菜来着”。
妻子经常跟朋友讲,正是我来广东之后学习的这一道白切鸡征服了她的味蕾。我倒觉得,白切鸡三浸三泡、细切葱姜,考验的只是耐心而已。
所以,我始终认为,是我的番茄炒蛋征服了她。
文 龙哥
图 Li-Chuan Chen on Flickr 循CC协议使用,经简单裁剪及调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