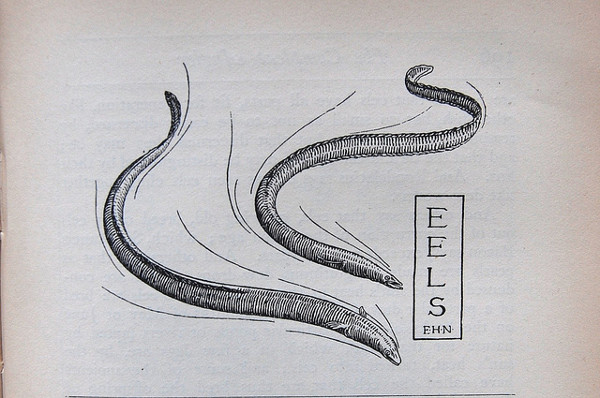从小到大,一直特别爱吃汤粉。尤其是吃早餐的时候,冬天的早上一碗冒着香气、热乎乎的汤粉下肚,给胃带来极大的抚慰,瞬间赶走了寒冷。夏天则喜欢慢条斯理地喝着醇香的汤水,细细地品着口感绵滑充满米香的汤河粉。吃完热乎乎的早餐,全身充满能量地投入工作,愉悦地展开一天的生活。
我家在山区农村。记得小时候,一天三餐都是以米饭为主。那时候物质匮乏,面、河粉之类的精加工食物比较少见,很久才吃一次。也有可能是农村人一天到晚要劳作,体力消耗大,唯有米饭最补充能量,所以便少吃面条或河粉之类的食物。而大米对于南方的农民来说,直接取自田里,是一种既可以饱腹又富有营养同时很方便的主粮。由于少吃其它食物,使我对第一次吃汤河粉的印象尤为深刻。
那是七八岁放暑假的时候,我去广州帮爸妈看店。在一个睡眼朦胧、灰蒙蒙的早晨(开店的人都是起早贪黑的),妈妈端来一碗隔壁店买来的汤河粉,香气扑鼻而来,焖得入味的牛腩和点缀的葱花铺在最上面,一尝,清香的汤底、绵滑的河粉令我胃口大开,米香肉香完美结合,完全征服了我的舌头,我至今记得那难忘的味道。现在想起来,我当时颇有狼吞虎咽的样子。那时,一碗料足味正的牛腩汤粉才五元,现在随着物价上涨,二十元的吃起来都没那么正宗。
随后的日子,我吃了不少汤粉,各种各样的。然后怎么也没有最初的味道,河粉没什么稻米香,各种各样的食品添加剂被滥用在食物中,食物也失去了最自然的美味。
后来毕业工作谈恋爱,男朋友看我那么爱吃汤粉,积极的说要带我去他老家吃最美味的横沥汤粉,还要带我去他老家看他两层半的“别墅”。我兴致勃勃地跟着去了,于是我终于吃到了他们口中啧啧称赞的横沥汤粉。真的很好吃,和小时候记忆中的牛腩汤河粉一样好吃。虽然它和牛腩汤河粉味道不一样,甚至口感更丰富,味道更加多层次,因为它的料更多,汤底由多种材料(虾粉、鱼肉丸和骨头)熬制,所以很好喝。后来发现很多地方都有横沥汤粉,原来横沥是一个地名,横沥汤粉并不是我男朋友家乡独有的,而是起源于他老家附近的横沥镇。了解后,才知道横沥汤粉是广东惠州最受欢迎的小吃,关于横沥汤粉还有一个惠州人都家喻户晓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横沥汤粉的创始人李子玉(博罗人),故事讲的是勤恳、踏实的李子玉热爱厨艺、不断钻研,最后创造了美味的横沥汤粉。
没想到小小的一碗汤粉却又这么美好的故事,我想就算如汤粉这么普通的食物,只要认真对待,也可以给普通人创造美好的生活,给食众满足的感受!
图&文 初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