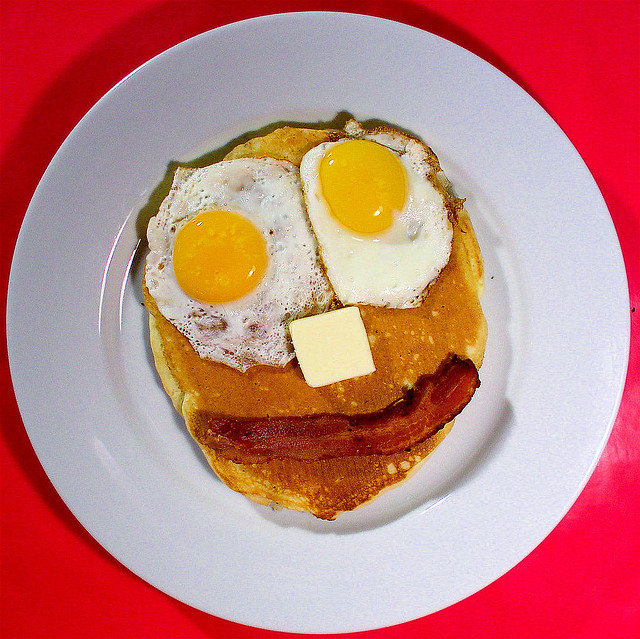大学时代的闺蜜清明节要来拜我。哦,我是说,拜访我。
商定了她大致到访的日子后,我羞涩地说:“那个,我有一个不情之请……”
“说。”
“能不能帮我!带一份!油!烫!鸭!(啊咧,节操都碎了)”
她震惊地“啊”了一声,旋即说好。
关于大学,我的记忆不多。
因为翘课很多,而且搬到校外独住了两年,所以既没有很多上课的记忆,也没有太多宿舍生活的记忆。
谈过两段恋爱,异地恋,都是以“大概还不错吧”开头和“还是不喜欢呀”结尾。所以时至今日连二位的面目都记不清楚了。是真的记不清了,也不记得他们的生日,也不记得恋爱时相处的光景。
唯一印象深刻的,是徐州的饮食。和那些淡漠的记忆交错在一起,让整段时光有了奇幻的色彩。
比如市中心的沃尔玛三楼曾有一家甜品店,牛奶是郊区农场的,每天都新鲜,非常好喝,比超市买到的任何一种牛奶都棒。那家还有沙冰,桂花沙冰和茉莉花沙冰都是我的心头好。ex从外地来看我的时候,通常我们会一起坐十几站公交去吃一顿。哦,那附近还有呷哺呷哺的小火锅。我喜欢一边吃番茄底汤的小火锅一边吃沙冰。
学校宿舍楼外的步行街有不错的油烫鸭。这是徐州才有的小吃。卤好的鸭子码在哪里,有人要就切一脚(四分之一只)或半只,过秤,斩成小块,扔到油锅里“刺啦刺啦”一顿炸,外皮稍稍炸酥,里面的鸭肉也透着油润劲儿,捞将出来,在锅延上压一压,把油篦去一些,然后倒到一个大盆子里,淋上各家秘制的酱料,搅匀,装袋,拎走。整个过程行云流水。油烫鸭一点也不高大上,从名字到做法到口味,都直白得一览无余。但下酒极好。
徐州菜(仅以我吃过的来说)大多走的是放荡不羁的路数,所以还蛮适合我这种仗剑走天涯的侠女风格。
看那些小饭店做菜就能看出来。不管是酱油还是糖、盐、孜然、还是辣椒面,好家伙,都是“咵嗤咵嗤”地几大勺就下去了。口味重,但是,好吃,下酒。最喜欢的是干煸四季豆、干煸花菜、醋炝藕条和腊皮肉丝。毕业后自己还常在家做,味道虽然差不离,但豪情可就完全不在一个次元了。
徐州的地锅系列也很棒,地锅鸡之类的。这些菜的共同特点就是整锅端上来,锅底汪着分量足实的鸡块啊肉啊什么的,锅边上贴着面饼。那面饼极有嚼劲儿,在汤汁里浸一浸比肉好吃。
有油烫鸭的那条步行街上馆子甚多,家家的地锅做得都不错。有一家特别擅长做干锅鲶鱼。自己到厨房挑一条鲶鱼,现杀现做,20分钟左右上桌,鱼肉鲜甜而嫩,汤汁咸辣浓郁,鲶鱼刺不多,而且皮好吃,那家的干锅鲶鱼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
还有一家,店面不大居然还是连锁——之所以知道是连锁,是因为除了和大学闺蜜在那儿吃过一次外,还在苏州吃过一次。苏州的那一次,陪我吃的是个平时基本素食的主儿,生怕委屈了我,偏拉着我去吃干锅,点了一堆,最后剩了许多,是永生难忘的味道。
徐州羊肉吃得多,宿舍区外那条街一到黄昏就成了烧烤一条街,大排档一家挨着一家搭起来,都是炭火和烤羊肉的气息。
那时吃烧烤是不论串卖的,论斤。两个女孩子一般半斤也就足够了。吃烧烤最好是在夏天或冬天。因为夏天的扎啤格外凉,冬天的羊肉格外暖——强烈的对比容易滋生巨大的幸福感和“不知今夕何夕”的恍惚。
我的初吻是在一次烧烤后没了的。漂亮的姑娘遇人不淑,晚上约我吃烧烤,酒量不济偏爱学人借酒浇愁。洁白的羊脂在火上逐渐逼出清亮的油脂,滴在烧红的炭上“滋啦”一声蹿起老高的火苗,又忽地缩回到炉中,羊肉微膻而带着鲜甜,孜然和辣椒面有侵略性的香气。扎啤冰冷地从喉管一直到胃——醺醺然的姑娘“老子”“老子”地骂了几句娘后又开始没由来地笑。
月亮慢慢上来,亏得羊肉抵住秋夜的寒,醉了的姑娘偏拉着我在操场上散步,草坪上手拉手走着的或观众台上隐约依偎着的都是校园里的小情侣们。她喝多了,眼神清亮,笑着说,来亲一个,倏然凑过来,嘴唇温软。
现在,她还是爱给我打电话抱怨男朋友不懂事啦幼稚啦小心眼啦blah blah,抱怨来抱怨去总归是舍不得分开。之前说清明要来,我说要是清明太忙就等明后见面好了,南京到泰州就是分分钟的事儿。她说:“见了你才不辜负春光呀。”我一笑,嘴巴还和读书时一样甜呢。
食物是最长情的,它曾经从你的味蕾,经过你的喉管,食道,胃。在离你心最近的地方,把时光也慢慢消化掉。
今年春天雨水格外多。我这里雨声渐密,落在外面的金属晾台上和楼下的香樟树上。远处的街道亮起街灯,灯落在潮湿的路面上微微摇晃。我喝了一杯稠酒,格外想要一份油烫鸭。
文 清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