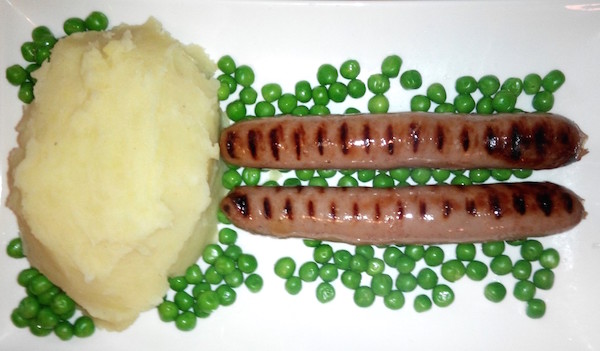吃饭容易幸福,这就是我对一日三餐最原始的眷恋。天生的好胃口,加上爸妈都做得一手好饭,平日里的家常菜都是我最爱。虽然N多次被小小的“规劝”,我还是有负众望,长成了家里唯一的一个胖子。天真无忧、幸福快乐的胖子。
大学毕业以后,由于工作原因,父母与我分隔两地,二千多公里的距离,让曾经走南闯北的我莫名的感到孤单,那一刻我突然懂了,原来四处走走和安身立命有着太过本质的区别。从前谈漂泊,都是在他乡,可孤身一人的我,现在觉得家乡亦是异旅。每个周末放假回家,总是希望窗口能亮起一盏灯,进屋就有老妈的热乎饭。可生活就是这样,充斥着这样和那样的无奈,虽然老妈退了休可以在家陪我,可老爸一个人在外工作该有多辛苦,我深爱老爸,总舍不得他一个人。所以无论是大三的时候打算定在深圳,亦或是毕业了回到家乡,只要父母在一起,怎么折腾,我都无怨无悔。
然而,领悟的再好也抵不过现实,下飞机到家的当天就血溅了洗碗池子,手被下水管割了个深深的口子,血肉模糊。打电话和妈妈哭诉,委屈到不行。我那一辈子把我惯的和什么似的妈,叹了一口气,淡定的说:“给你两个选择,第一立刻买票回来,第二马上憋回去,把手处理好。”那以后我时常想起当时我妈牛X的语气,每每都有感悟。
刚参加工作,每一天都有收获,可也常常受挫,晚上躺在寝室的小床上便会思绪万千,总觉得回家心有不甘,总觉得要做的梦都在远方,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晚上听见火车的汽笛声,就有一种说走就走的冲动。虽然我从来不和父母说,可我是真想他们。单位一领导对我说:“现在你还小,等以后你会知道这世界上能依靠的只有你自己,要学着独立。”聆听,受教。
一年以后的今天,曾经十指不沾阳春水,自理低能的我,已经完全可以处理家务,做一手好饭不成问题。家里豆浆机、榨汁机、面包机、烤箱、厨房设备一应俱全,送自己个小资的下午茶不成问题。偶尔晨起不愿喝粥,便榨一杯豆浆,香气缭绕,醇香无比,配上几块小饼干或是几片粗面包,一整天都神清气爽,精气神十足。同事取笑说我比以前进步了,早餐喝的上豆浆了。我说,其实,我喝的不是豆浆,是成长。
生活总在岁月中不停的变换着模样,不变的是我们永远在这多变的生活中。坦途也好,逆旅也好,都让我们不断成熟,变成更好的人。也许远方仍然闪现着灿烂的光,可此时,就让我们享受当下吧,做想做的事,爱能爱的人,大口吃饭,健康生活。
图&文/L.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