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婆做得一手好菜,哪怕那些家常风味的小炒,在她手下也摇曳出别样的滋味。在外婆做的所有菜里面,我最喜欢吃的是她做的豆花。
在我家,豆花其实就是豆腐脑,不过与早点摊上专门做出来的豆腐脑不同,豆花是用来压制豆腐的,说白了就是还未成形的豆腐。
豆花一团一团的,就像白白软软的棉花一样,它们一团一簇地躺在清而微浊的浆水里,等待着外婆把它们放在专门用来压豆腐用的竹筐里,等待着某一块巨型石头狠狠的压在它们身上,挤走身体里多余的水,然后无数朵小豆花就会融合成一块大豆腐。
外婆做豆腐的手艺一绝,做出来的豆腐又嫩又滑,在小镇不说家喻户晓,但也是人人皆知。记忆中的外婆梳着和刘胡兰一样的发式,夏天的时候总是穿着一件青色纱质的小褂,冬天就换成一件蓝黑色的。

外婆说,豆腐要做的好吃,就离不开有优质的水。每天清晨,就外公和她提着水桶去离家不远处的水井里打水,微微驼背的她,晃悠悠地跟在外公担子身后,提着小桶的水。
那时的我,尚还年幼,常常像一只小麻雀一样蹦蹦跳跳地,跟在外婆去挑水。所有清早挑水的辛劳只为做出最嫩的豆腐。
那时候觉得外婆就像一位神奇的魔法师,每天在小小的厨房里泡豆子、磨豆子、熬豆浆。那些小小的豆子在她的手里变化无穷,角落里的那口大铁锅也总是发出各种各样的声音,前一秒是水就要沸腾的滋滋声, 下一秒是咕咚咕咚的冒泡声。
醇香的豆汁咕噜咕噜地在锅里沸腾,那股豆香味儿已按捺不住了,在热气的作用下,簇拥在狭小的厨房之间。

性急的我,这时候,被豆香味儿牵着鼻子,就会蹦跶到小厨房这里,探头探脑地张望着外婆的豆腐。这时候,外婆总会舀上一大勺豆浆,搁上一点糖,端过来打发我去别处玩。浓郁的豆浆,滑过舌尖,在口腔里化润到每一处味蕾之上,缓缓滑进喉眼深处,甜滋滋的小半碗我全喝光了,打个饱嗝,整个人暖乎乎的,舒服极了。
当我在院子墙根处打了个盹儿,迷迷糊糊中被外婆张罗切豆腐的动静给吵醒。原来,豆腐做好了诶。外婆收拾完卖豆腐的家伙后,这时候外公就会从外婆手里接过这挑担子,挑到镇外的市集叫卖。
待一切收拾妥当,外婆才端出提前预留给我的豆花,白嫩嫩的豆花,放点用肉汤,蘑菇,淀粉熬成的卤子,再撒上一小层葱花,看起来格外有食欲。
“外婆,你做的豆腐就是好吃,你是不是会魔法的仙女呢?为什么我妈妈就不会做豆腐呢?”这时候,外婆常常被我逗得合不拢嘴,她温柔地摸着我的头发,说道:“好水配好豆腐,水好了,豆腐自然就做得好。乖娃娃,多吃豆腐,才会长得白白嫩嫩的。……”
 后来,我依旧穷根追问外婆做豆腐的秘诀,可哪怕我问得再多,外婆也只有那句话,“好水配好豆腐”。在外婆看来,似乎做豆腐就是这么简单的秘诀,“好水”自然成就“好豆腐”,手艺与火候就直待顺其自然地顺承了。久而久之,在我心中,外婆与好吃的豆腐也就成了无因果的相关联与必定存在。
后来,我依旧穷根追问外婆做豆腐的秘诀,可哪怕我问得再多,外婆也只有那句话,“好水配好豆腐”。在外婆看来,似乎做豆腐就是这么简单的秘诀,“好水”自然成就“好豆腐”,手艺与火候就直待顺其自然地顺承了。久而久之,在我心中,外婆与好吃的豆腐也就成了无因果的相关联与必定存在。
可自从外公去世后,外婆便不再做豆腐了。但是她还会给我做很多好吃的,包饺子,做面片汤,做红烧肉,就是除了豆腐的其它拿手好菜。
在我强烈央求她她给我做豆花吃时,外婆总会深深抽了一口烟,然后慢慢悠悠地吐尽烟圈,烟熏缭绕,半响之后,才冷不丁灵地回我说,“外婆老了,做不动了,小丫终于长得白白嫩嫩了,好豆腐要配好水,没有好水怎么做不了好豆腐啊”。

说完这句话这句话之后,外婆又掏出了一根烟,点了起来,狠狠地吸了一口。听妈妈说,外婆的烟是从送走外公之后就开始抽上了,而且最近这段时间还是越抽越凶。
外公的离开,似乎也将外婆的一大半精神也给带走了。曾经那个健谈勤快的小老太太,如今好像变成了一只孤独疲惫的老猫。日复一日的斜椅火炕的一头,要么眯着眼抽着土旱烟,要么就是沉沉窝在炕上睡着觉。
有一天在电话里,外婆忽然对我说说:“小丫,我前几天想吃饺子,活好面以后,竟然不会包了,你说说,多好笑。”她边说边笑,而我边听边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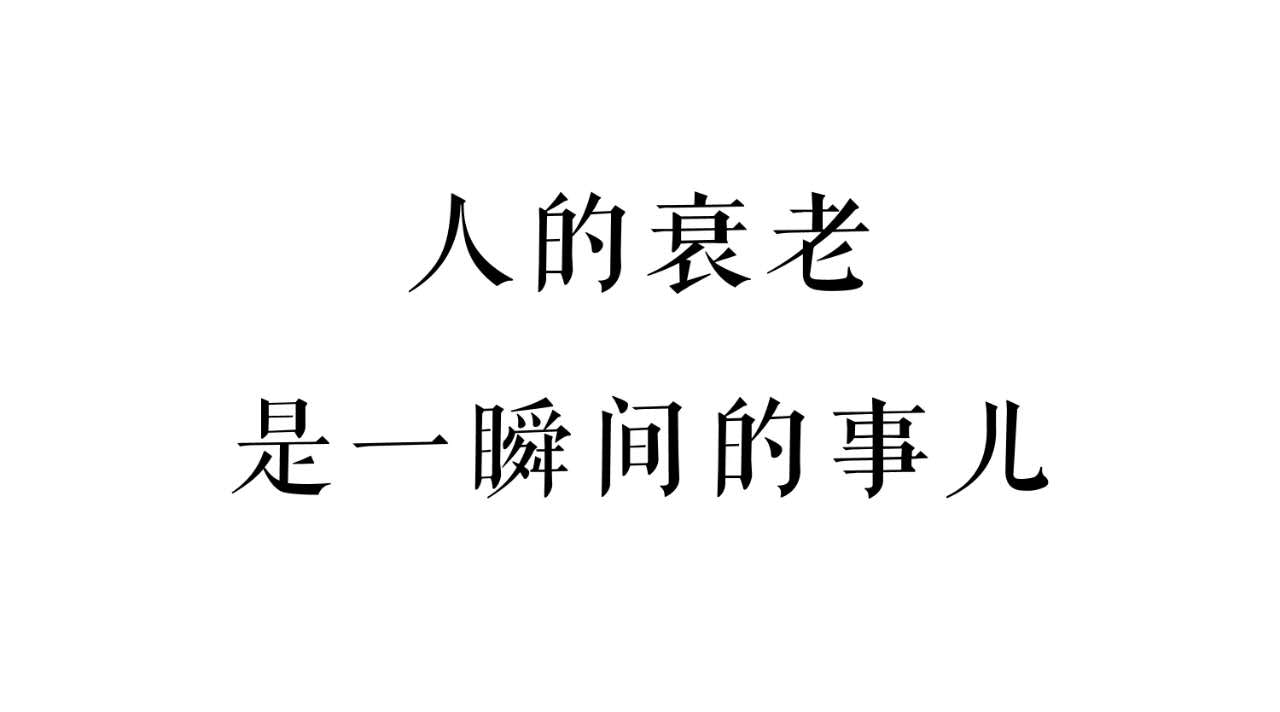
有时候,人的衰老有时候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后知后觉如我,直到今天才明白“好豆腐需要好水”的真正含义。做得一手好豆腐的外婆,在外公离去之后,就再无余力自己一个人挑水,磨豆做豆腐。
忽然之间,想起那些年不断追问外婆的豆腐秘诀的光景。我想,最好的豆腐,少不了“好水”,更少不了外公外婆两人你挑水,我磨豆的默契。外婆的“顺其自然”,其实就是磨砺到最后的熟练。这种熟练,如感情,如生命。
文/孔小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