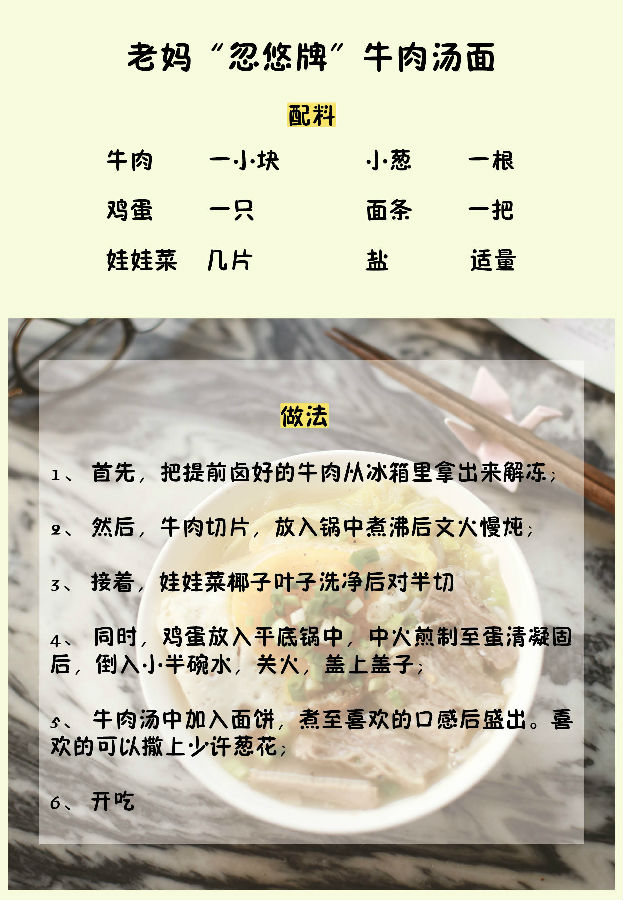这里,一定是被上天眷顾的土地。
暖融融的春风,吹动金灿灿的油菜花田,八百里巢湖波光潋滟。
冬笋清甜无渣、葛根苦中带甘、葡萄汁水淋漓,它们是属于冬天的记忆。

而春天,一只麻鸭悠然地浮在水面上,忽地抬脚掀翅撩动水花,仿佛得意于知道了什么了不得的秘密。
我在岸边快速打量一下它的身形,默默地回味着无为板鸭油亮酱色的皮,还有那锁住了淡淡熏烟香气的肉。
这就是我的家乡。
很多原料只有这里才产,很多菜色只有这里才能吃到。

长江、淮河和新安江三大水系在安徽织成密布的水网,淮北平原、江淮丘陵、皖南群峰组成了多样的地貌,共同孕育了这里丰富的物产。
而甲鱼这种食材,游蹿于山涧、湖泊、池塘、浅滩,得有清水、有泥沙、有温暖宜人的气候。
海边和高寒酷暑之地,它是不屑于去的。按着我这些年的行踪,还是回家时比较易吃得到。
家中一绝:外公的红烧甲鱼
我外公亲手所烧的甲鱼乃是一绝。

选用力大生猛的野生甲鱼。开水烫去壳上面的膜,这样在焖透后才能直接享受裙边软嫩弹牙的口感,不会有硬皮扎喉咙。
甲鱼背甲并不斩碎,为的是保留脊柱中的髓质和精华,还有背甲内侧脊柱边的两道细滑的活肉。剖肚放血,剔除脂肪,去除腥气,但保留肝胆。

取带皮带膘的咸肉,必得是新近腌制入味的,才能瘦肉紧而不柴,肥肉凝固饱满。切大小适中的片,在生铁锅炒至油出、浓香出,再放老姜、干辣椒碎和少许重庆花椒,油火爆炒。
底料咸香微辣的味道吊足后,方下甲鱼烧焙。熟后放黄酒、老抽、生抽、胡椒继续炒制,肉香飘散时加开水,大火烧、转文火焖,再转大火收汁。
加葱碎,起盘。成品浓油赤酱、香气扑鼻,完美地包留、放大了甲鱼原汁原味的鲜美。

皮脂软糯,夹起一片,颤颤巍巍,抿上一口,入口即化。腿肉丝丝入味,细而不散,酥而不肥,混合着外皮的软糯和汁水的鲜香,带给人难以忘怀的口感。
甲鱼肝绵密肥嫩,小口享受后将鳖胆一口吞下,明目清肺。这口美味是家人留给我的独一份的宠爱。
曾经,那是穷苦岁月里难得的美味
每次回到家乡,家人总拿出万丈的热情要给我“好好补一补”。这时久不下厨的外公就会积极主动地和外婆赶最早的集市,然后挽起袖子在烟熏火燎的厨房里炮制大餐。

鱼虾鳖贝和鸡鸭肉蛋煎炸炖煮后流水似的端出来,爱子爱女贤媳贤婿忙忙碌碌地移桌子摆椅子,孙子们满屋子乱蹿打闹。
外公红光满面地坐在首座,端着他的酒杯,笑声洪亮。他胃口很好,家宴上频频给我们布菜。我几乎头也不抬地埋首碗里,甲鱼的胶质黏住了嘴唇,怎么也跟不上他们夹菜的速度。
“这块肉好,宝宝吃!”甲鱼腿飞来。
“裙边美容,给宝宝!”他指挥外婆给我布菜。
“鳖精不能浪费。”一块连壳带边的整块背甲彻底盖住了我的碗。
外公志得意满地叼着牙签,把饭菜舀给孩子们。能吃,在他看来是大大的福气。
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猪肉是稀罕的,泥鳅、甲鱼、黄鳝却不值钱。这些东西腥气,旁人是不大愿意吃的。我父亲小时候常年饿着肚子,用它们喂鸭子,然后盼着鸭子长大,勉强维持生计。

而外公,用年底的肉票买来猪肉,省下一块腌了,用这一点点咸肉把泥鳅、甲鱼、黄鳝烧得鲜香扑鼻,引的孩子们狼吞虎咽。
我母亲得意地说:“我爸妈是多会过日子的人啊!”
他们用生活的智慧,在穷苦的岁月里给予孩子衣食保暖。纵然时代已不需要他们再从玉米杆中提取一点点甜味、从花生碎中榨取一点点油水,甚至泥鳅、甲鱼、黄鳝和野菜也成了稀罕的食材,外公的手艺却从未褪色。
他首先想到的,还是你
我一脉相承地延续了母亲这方对美食的热情,对喜爱的菜色有着执着的记忆。走过天南地北,吃过大街小巷,外公的红烧甲鱼在我的味觉里依然是不可替代的美味。
这一年来,外公的身体渐不如从前。红堂堂的脸庞黄瘦了下来,洪亮的嗓门细弱少音。
曾经蒲扇般的大手只要扬起就能让顽童害怕它蕴含的力量,现在枯瘦得只留下了凸起的青筋和薄薄的皮。

谁也不忍心再累着老人了,家宴改在了酒店里。酒店里的红烧甲鱼上来,脂肪没处理干净,火候略老,酱油略多,我瞄了一眼。
外公安安静静地坐在尊位,只在儿女敬酒时偶尔露出微不可见的笑容。外婆把他能吃的菜夹到碟子里,他握着勺子慢慢地吃。
在甲鱼转到眼前时,他停住了,轻轻拍了拍外婆的手臂,几不可闻地说:“宝宝吃。”
我含着那块被夹来的肉,觉得又一次吃到了熟悉的味道。
这就是外公的红烧甲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