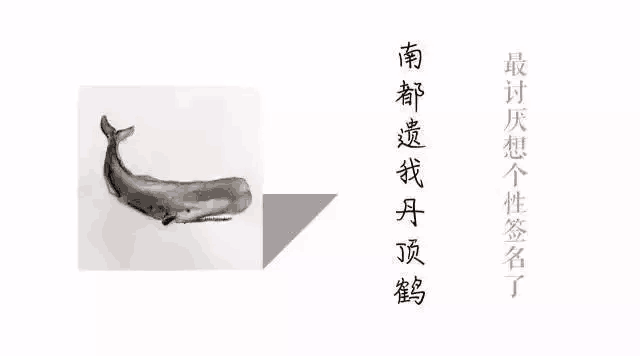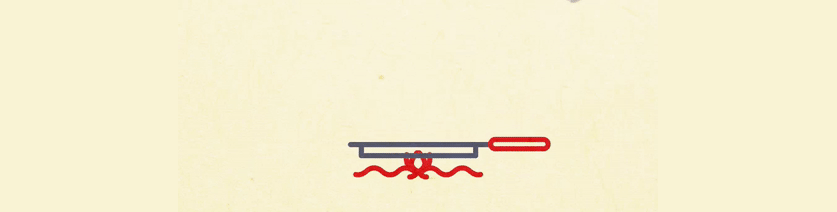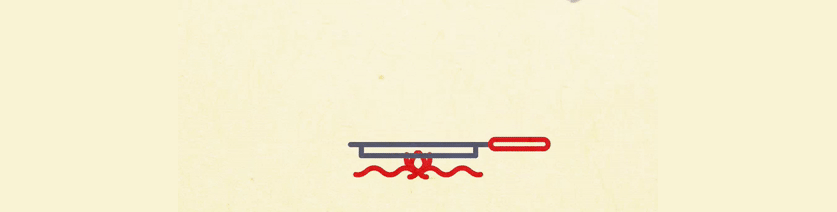二十万吃货的精神故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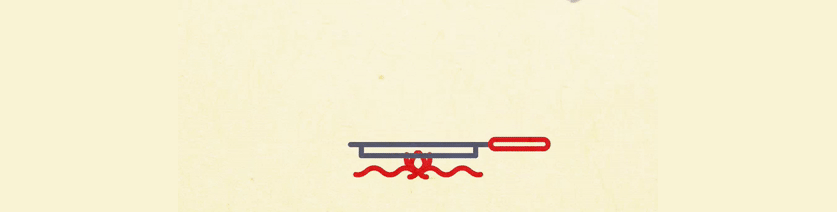
上周六,南都小姐讲了台南,这一次她要讲台中。
上面那句话,平淡的像白开水一样,我想在台南和台中前面加个形容词,但是想了半天还是不知道加什么好。也许台湾就是这样,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理解,听过无数次描述,但你不踏上,它永远是一片不可言传的朦胧远景。
南都小姐,不管在台湾哪个城市,都总会有个跟她一样直率大方的妹子,遇到一些朴实又“佛心来着”的店。今天,她带我们走台中。
——深夜君
- 正文 -
大丁不是男孩子,大丁是个漂亮姑娘。
没人知道这个绰号是怎么来的。只是我有时会想:大是很大,丁是很小块的意思,大丁的话究竟想要很大还是很小呢?
又或许人生就是矛盾如此,渴求很多时拥有的却很少,想过简单生活的人往往背负过多。
大丁是土生土长的台中人,台中也是我居住了五年的地方。我无法把它当作一个景区那样介绍,这座城市熟悉地会让我失语。今天我只想讲台中女孩大丁的故事。
那天晚上我们约在她公司后门的一家新开的日式烧饺店,名字叫次男。据说因为它是台中“MEN拉面”老板开的第二家店,店名的用意在于把它当作自己的第二个儿子。
不过在我们人类社会里,长子承载厚望,老幺得到万般宠爱,老二则往往是两头不沾,还经常被忽略的倒霉鬼。大丁就是老二,在一个由妈妈、姐姐和妹妹组成的纯女性家庭里。
大丁的爸爸在她五岁那年意外去世,妈妈靠在镇上做文员养活自己和三个女儿。我是后来才知道那男人生前是个赌鬼,总是抢老婆的工资出门滥赌,而奶奶最常说的话就是“男人赌点钱没什么的”。
不过幸好台湾的福利机制对只有一个劳动力的家庭格外照顾,大丁像别的孩子一样吃饭、上学、谈恋爱,顺利地长大。

那天店里的人有点多,我们等了一段时间,两份招牌原汁牛肉烧饺和猪肉赤味增汤才上桌。

烧饺子其实就是煎饺,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料理技法,馅料是否诚意十足是决定最后爆浆效果的关键。
次男的烧饺颗颗浑圆饱满,外皮透着光泽,隐约可以看到粉红色的内馅。用筷子夹起一颗,就可以感觉到不同寻常的重量,那是店家“佛心来着”(台湾常用语:有慈悲心的,常指店家的不计成本)的表现。

先咬一小口,感觉到金黄色脆皮的焦香。水饺和煎饺最大的区别在于烹饪时的导热物质。水饺用水,最高只有100度;而煎饺是用铁,可以达到200度以上。
灼热的温度和加入的水淀粉,让饺子的底面形成雪花一样的美丽脆皮,在日本叫作雪花/冰花煎饺。高温同样逼走了多余的水分,让内馅被激发出更多的肉汁。
果然,原汁牛肉烧饺的表现恰如其名。一口咬下,浓郁的肉汁便混合着澎湃的馅料充盈满口。这和汤包馅汤分离的感觉很不一样,因为肉汁会随着咀嚼越来越多,牛肉的香味逐渐笼罩口鼻。
我还在沉浸在细致品味中时,大丁已经迅速解决一盘了。
“老板,再来一份次男烧面,半熟蛋。”

我又差点忘记她是个外表瘦弱饭量奇大的女生了。

在我认识的女生里,大丁是个饭桶一般的神奇存在。我们四年的室友生活里经常出现这样的对话:
“你觉得这家火锅怎么样?我很喜欢呀。”“还不错吃,就是没吃饱。”
或者是:
“这里的米饭可以无限续,你吃不饱再拿哦。”
“恩,刚刚拿两次了,店员正盯着我看呢。”
更恐怖的是:
“别点这个家庭套餐啊,我们两个人吃不完的。”
“可我没有要跟你分啊。”

除此之外,她每次都会毫不介意地帮我消灭剩下的食物,我在家时这是爸爸负责做的事。我不知道她家是不是经历过没米下锅的时光,只记得她跟我说过,小时候因为她一直吃没停下,奶奶就把桌上的小鱿鱼藏起来。

除了食量巨大,大丁还身负众多一般女生不擅长的技能——车技上乘(无论机车、汽车)、电脑小能手(我们可是文科生)、木工老司机(我们寝室那一直坏掉的门啊~)。
高中时她就去考了手动档驾照,这样就能开着她家那台历经风霜的老吉普代替辛苦工作的妈妈接妹妹放学。
她从没为失去父亲哀叹过。“如果爸爸没有去世,我们应该会活得很辛苦。”她曾经对我这样说。
当时我觉得自己应该回应点什么,反驳或者安慰什么都好,但一切熟知的家庭定义此刻都变得道貌岸然起来。她说的是事实,这让我感到一阵蔓延不绝的钝痛。
所以我没什么都没有说,大丁本来就不需要听那些。她已经开开心心、堂堂正正地长大了,比很多男人更像个真正的男人一样,孝顺、稳重、有担当,是家里的顶梁柱,吃得也最多。
我想大丁的意思也可能是这样——大是年龄最长,丁是能承担赋役的成年男子。在父亲缺失的家庭里,从次女变成次男,再逐渐扛起一家子甜蜜的负担。
专栏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