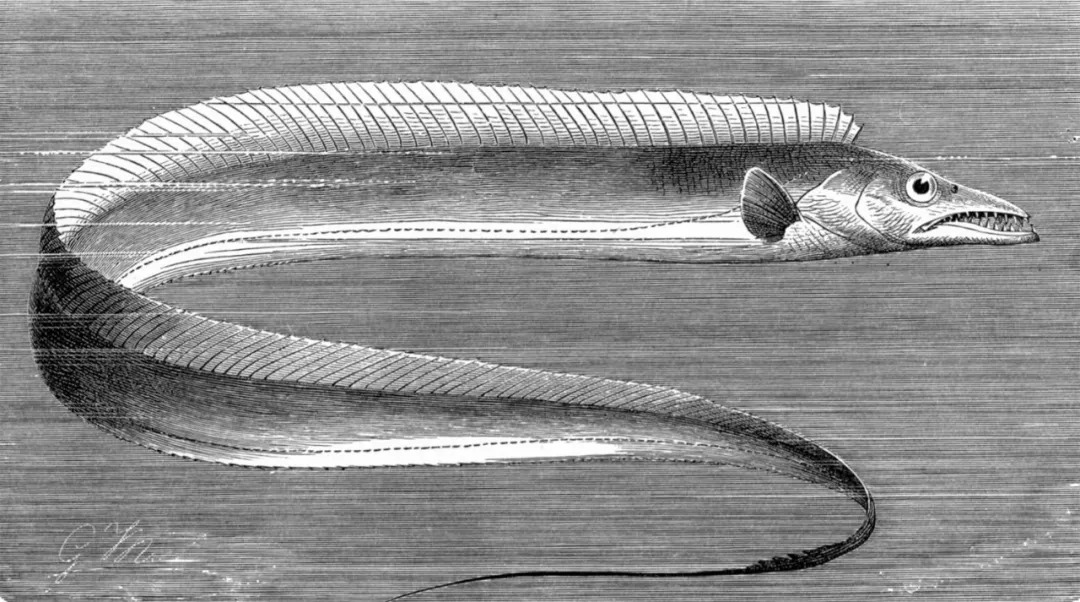当集市上开始频频出现石榴的身影,我就知道离桂花香满园螃蟹沿塘走的中秋不远了。
认真的说吃石榴和吃小龙虾一样付出和收获不成正比,忙乎半天塞到嘴里咽进肚里的只有那一点点汁水,跟点眼药水儿似的,刚抿出来点儿甜味儿就得忙着吐籽,就算吃光三斤石榴还是饿的肚皮贴到后脊梁。并且石榴的外皮浸出液又带些黄色,常常剥完了石榴手指头尖连指甲缝都被染成难以描述的颜色,一手黏糊糊很是郁闷。
所以很多人不爱吃石榴,剥起来麻烦吃起来更麻烦的玩意儿,时间成本消耗太多,把人吃的心急火燎。奔着这个市场反馈,这几年软籽石榴开始混的风生水起,号称吃石榴不吐石榴籽,剥一大捧仰头倒嘴里直接咽,或者拿来榨汁也很不错,出汁率极高。
但大概是我念旧,总觉得吃石榴如果少了吐籽环节,和睡觉不闭眼一样难以想象。尤其是小时候常吃的陕西临潼石榴,确实好吃,外皮青黄带皱纹,个大籽红汁水甜,又耐存放,念书时候住校,返校时候书包里揣一袋石榴可以吃上一礼拜没压力。如今的软籽石榴虽然外表红彤彤,籽大汁多,但真说不吐籽吧又总觉得嘴巴里一堆渣渣咽也不是不咽也不是,而且石榴籽的皮薄的一碰就破,经不起多少折腾就洇坏了,更别说我这种最怕吃水果时溅的到处汁水的强迫症患者,能完整不湿手的把籽剥出来就很不容易了,所以这么多年我始终镇守硬籽石榴阵营不动摇。
从小我就喜欢吃石榴,不是因为它真的美味到让我难忘。对一个童年时期淘气的要上天,不需要补课不需要发展有层次的兴趣爱好,又没有什么零食夜宵来丰富味蕾感受的贪吃小朋友来说,如何打发百无聊赖的漫长童年时光,绝对是个旷世难题,而吃石榴绝对是妙法之一,如何妙,具体陈述如下:
认真剥开并认真吃掉一整个石榴需要花很长时间,认真的含义是最大限度的保持石榴籽的完整,汁水不四溅,石榴籽上不残留石榴皮的渣屑,否则苦涩味道会掩盖甜味,吃的时候不浪费一颗石榴籽,不错过一丝果肉,每枚吐出来的白色内籽都是干净的。写到这儿我突然觉得小时候的自己真的是无趣的有点变态了…
在这长长的时间里,可以说味蕾对甜的感受是没有间断的,丢一颗进嘴里咬下去一抹甜,再丢一颗咬下去又是一抹甜,如果和啃西瓜一样三下五除二就啃完一个石榴,就算西瓜汁比石榴汁甜的多也过瘾的多,但再惊天动地的甜最多也只能维持一下子。
大概我从小就能从吃石榴这件事中充分的领会到细水长流的幸福才是真幸福,越是没尝过生活里的甜,就越是珍惜那一点点甜,一下子和一阵子,我果断选了一阵子。
和石榴这种一阵子特性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吃食还有一款,名叫玉米。我直到如今都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常说我,拿着一穗玉米能吃整整一下午,一粒一粒吃,别人吃玉米用啃的,我吃玉米用抠的,越抠到最后越慢,当把最后一粒吃掉的时候脸上那恋恋不舍的表情好像这辈子没吃过玉米似的。
后来我长大了,说起来什么好吃的也算都吃了七七八八了,吃玉米也从抠晋级为啃了,倒是对石榴还是不改初衷。
家里种过一棵石榴树,每年九月都会结石榴,石榴熟了必须摘下来,不然会落果。大学毕业后我因为工作远赴离家千里外的城市,十一假期都会回家。九月时爸爸摘了石榴,妈妈就统统放进去储藏间,说要留给我,从来不许爸爸吃,石榴躺在储藏室里起码半个月才能等到十一休假返家的我。爸爸每每看到我猫在家里沙发上边看电视边剥石榴都有点吃醋,不停伸手去拿我剥好的石榴籽吃,说,这石榴放了那么久,你妈都不许我先尝一个。我安慰他,因为妈妈知道我会把石榴剥好了给你吃,省得你动手剥,辛苦。
过了几年那棵石榴树死了,我再也没吃到过家里的石榴,于是便把水果铺里的硬籽石榴吃个遍。这么多年过去了,早练就一手剥石榴的好本事,石榴籽颗颗干净不带皮不破相,汁水不四溅。除了指尖功夫,更多凭的是一份耐心和克制,尤其是肚里藏着事火急攻心的时候静静坐下来慢悠悠认真剥石榴,我都瞬间有种修炼的错觉,就算只为了那舌尖一抹甜,如果能甜一阵子而不是一下子,那花点时间好好把苦涩的外皮全都剥了去,也算值得。
这些年定居成都,每到临近中秋,窗外的两棵桂花树都默默散着幽香,香味伴着秋天清爽的风飘进屋里来,坐在窗前静静剥石榴,胖猫横在旁边睡大觉,我从没想过自己会如此乐在其中,只是,剥好的石榴,没能让我在乎的人吃到。
又是一年中秋要到了,前几夜风大雨疾,我很想家了。
忘忧石榴深浅红,草花红紫亦成丛
明年开时不望见,只望郎君说著侬
《吴娃曲》 陆游
文 / 雅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