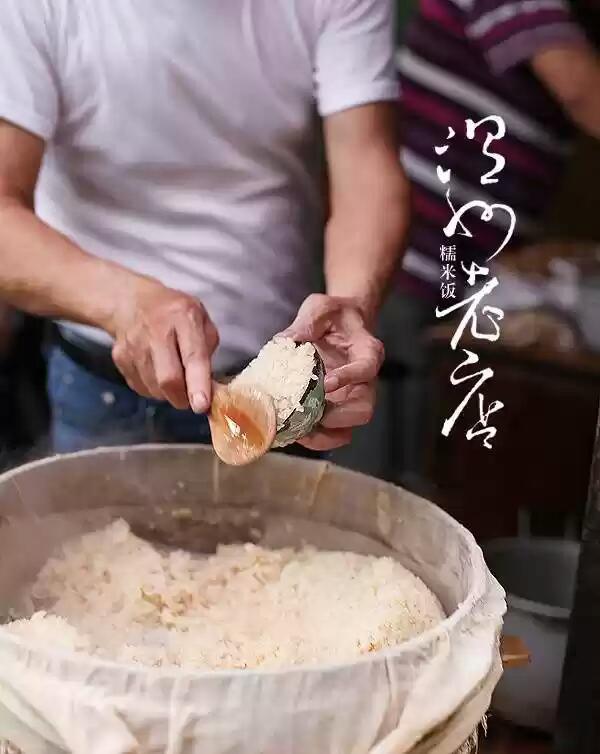农历四五月间,小麦拔节,开始疯长。
黄土高原上的洋槐花开了,一嘟噜一嘟噜洁白而繁盛,堆在高高的洋槐树上,像是一堆泡沫从碧莹莹的啤酒杯中溢了出来,整个村子都被浸泡在这清香之中。
这幅画面可能是很多游子心中都能浮现出的意象,不少人的故乡,都有一两棵高大勇毅的古槐,树干乌黑,擎起故乡碧蓝无际的天空,离开家的时候,千里奔袭回来过年的时候,它总是那样屹立在你目光最先到达的地方。
洋槐花是可以吃的。香气四溢,味道真是甜,不过微微带着一丝生腥味儿,小孩子不去管它,把镰刀缚在一根长长的竹竿上,轻轻一钩,一大捧花束就下来了。洋槐树新长出来的枝条上有刺,不适合攀爬,也没必要爬上去摘。但也有些调皮小男孩一天到晚趴在树上不下来,一仰头,一整串花苞就送到了嘴里,清甜芬芳的气息直渗到肺里去。
陕西有一道名点:槐花麦饭。洋槐花如同麦穗,一粒粒小花苞整齐排列在花序上,需要先捋下来用水洗净,再用开水稍烫,去除那一点子生腥味儿;土豆用专门的“擦子”擦成扁而细长的土豆丝,然后把土豆丝和洋槐花放在一起,倒入面粉搅拌,在土豆丝和槐花上面均匀地裹上一层,上锅蒸。
蒸熟的槐花麦饭,需要伴着汤汁一起吃,汤汁的配方各家不同,但是总少不了色泽红艳的秦川辣子和香气浓烈的大蒜,再配上碧油油的葱花,一起倒进酸汤里,浇在洋芋擦擦上面。吃“槐花洋芋擦擦”宜用勺子,一下挖一大勺,蒸过的“洋芋擦擦”里,弥漫着槐花的清香,酱汁的酸辣和洋芋擦擦的浓香互相激荡,让人胃口大开。
这种方法也适合用来烹制不太可口的野菜,称为“菜疙瘩”,是穷苦人家的吃法,因为粮食有限,就用面裹了野菜来蒸,骗骗肚子,现在农村很少有人吃了,城市的高档餐厅里倒是推出了贵得有点离谱的各式农家菜,吃过几次,大概是经过了改良,味道还挺不错。
把花拿来制作美食的,中国应该算比较早出现的了,西餐的餐盘里往往有花朵点缀,但却不是用来吃的,摆摆样子。
琦君在回忆小时候的散文里提起自己小时候母亲常常把莲花和玉兰花花瓣裹了薄薄一层面粉用油微炸,称之“玉兰酥”,有微微一丝甜味,父亲讽之为“焚琴煮鹤大煞风景”,不过琦君也从湖里采了莲蓬的枯梗,莲花“中通外直”,这枯梗里装了烟丝给父亲吸,有清热败火之效,每读至此处都觉得实在巧妙而有诗意。
茉莉花桂花香气浓郁,用来做糕点也很适合,但这都是西北地区所没有的,槐花真的是黄土高原上香味最为浓郁的品种了吧,陕西产全国最好的槐花蜜。小孩子偷看大人喝茉莉花茶,以为那里面的花便是洋槐花,便私自晒了槐花搀进茶叶中去,被发现总要领一顿胖揍。
栀子花也属香气浓郁的花朵,可以用来做很多美食,但都是精致小点心,里面带着富足江南人的闲情逸致,像槐花麦饭一样真刀实枪地用来充饥恐怕就不行了。
何炅的歌曲《栀子花开》清新纯美,但若论把栀子花写活的还得数吃货界最有名的大作家汪曾祺,他在《夏天》中这样写栀子花:
栀子花粗粗大大,又香得掸都掸不开,于是为文雅人所不取,以为品格不高。栀子花说:“去你妈的,我就是要这样香,香得痛痛快快,你们他妈的管得着吗!”
只这一段,其他人不用写栀子花了。
槐花落了,地上留下一堆残雪,洋槐的叶子愈发碧绿,蝉噪林逾静,快要开始收麦子了。
文 李铁柱
图 Yang Lan 循CC协议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