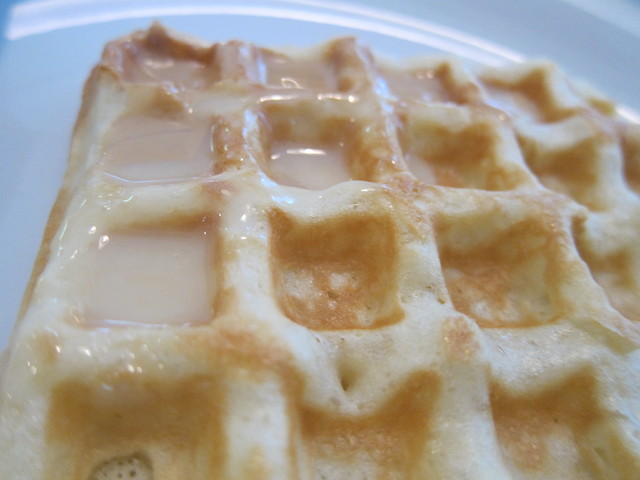图&文 Jacqueline Yeung
在香港,大排档并不是廉价的代名词。相反,比起连锁酒楼,大排档出品的价格往往让你膛目结舌。写在长条牌子上的各款菜式被挂于墙上,底下往往标着“时价”。这让不少食客点菜时思考再三,但仍免不了埋单时吓你一跳的惊心动魄。
这些大排档中,潮州打冷占去了半壁江山。这不得不佩服潮州人顽强的生存能力和精明的生意头脑。在租金动辄十万百万的香港,站稳脚跟坚定弘扬家乡传统菜式,恐怕也只有潮汕人有这般能耐。
两年前经常到旺角太子一家打冷店晚饭兼宵夜,去的时间较早,铺面还没有多少顾客,只见店主和伙计在吃晚饭。接近午夜,店开始热闹起来,不少上完夜班的人都会在此聚脚,一上来就要几瓶啤酒,大有不醉无归之意。而他们,往往选择坐在店外。看着街上逐渐稀疏的人群,听着店铺拉闸声,或许这样宵夜的风味更甚。
这家店有两个厨房,一冷一热分工有序。以透明玻璃间隔的开放式厨房是冷菜房,俗称明档方式。铁架上挂满卤鹅、卤水鸭翅等卤味,料理台上摆了一兜兜虾菇、咸虾。斩料师娴熟地切片,淋汁。开放厨房的旁边则是热火朝天的现炒现卖,不时火光涌现,镬气四溢。我喜欢美食的同时,也喜欢观赏美食诞生的过程,所以每次总是选择离“热房”最近的位置。
鹅的赏食期有限,能否吃上百日鹅是运气,所以我不强求酸甜醋蘸卤水鹅。但是来到这里,我会强求一碟“豉椒炒蚬”。下单后,厨师应一声“收到”,即到厨房开镬,倒一壶开水将大蚬煮至开壳。捞起蚬后,随即用蒜姜起镬,红椒圈豆豉等走起。大镬飞起,抛撒间火苗窜出,即加入大蚬爆炒,再注入少许上汤、勺几茶匙生粉,炒透上碟。
事实上,吃豉椒炒蚬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豉汁之上也。蚬肉已由壳中脱出,蚬壳才是主角。不管壳中有无物,只管蚬身蚬壳是否挂满欲滴豉汁。夹起一个又一个,吮吸咸辣得宜的豉汁,吃得津津有味,乐不停箸。蚬肉清沙后,清甜撞上鲜辣迸出无穷的美味是送饭佳品。虽然是塞牙缝都不够,但并不阻碍食客的热情。吃到最后,往往剩下闭壳的那一些。闭壳,不是未熟,反而最后还送你一份“抽奖”般的期待。打开,还幸存蚬肉,那心情豁然开朗,舌尖能再度忙碌起来。打开,若是一肚子豉汁,没有关系,照样送进口中一滴不漏,皆大欢喜。
怎样都不会得罪食客,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大概也只有它吧。
—————–
关于「打冷」,维基百科的解释是:
打冷是指去香港及广东等地,到潮州大排档吃饭或吃宵夜。这些潮州大排档主要经营的凉菜式,一般有卤水类,腌制类以及各类潮州粿品等。如卤水鹅、卤水墨鱼、卤水豆干、卤水猪肉;腌制虾菇、腌制蚬、腌制河蟹;麻叶、红鱼、冻蟹、白粥、蚝仔粥、番薯粥等等。
关于“打冷”这一词的由来,有几种说法,较为普遍的说法有二。一是潮州话里的“冷”,是“人”的意思,如大家熟悉的“架忌冷”就是“自己人”的意思。“打冷”也就是“打人”的意思。五六十年代,许多潮州人偷渡到香港做黑道小混混,他们会经常到老乡的店铺吃宵夜,同时等待“开片”——打架。他们收到要开片的消息便会说去“打冷”。久而久之,吃潮州宵夜称为“打冷”。不过,还有另一种说法,大致也是说“打人”的意思,只是前者的具体版。五十年代香港黑道人物常到餐馆吃霸王餐,香港第一大帮派“新义安”就是潮州帮,气势得很。当年餐馆伙计发现有人吃霸王餐便会大喊“打冷”以召集伙伴一起对付白吃白喝的人。慢慢香港人就把这种潮州宵夜档称为“打冷档”。
另一种说法,则和“打人”没有半毛钱关系。维基百科贴出一个来由:“打冷”是潮州话“担箩”的译音,潮州人担着竹箩,做小贩卖卥味。人们叫他们做“担箩的”(打冷的)。
另外还有人说 “冷”,是指放置冷了的食物。“打”字,则和“打的”的“打”一样,并不是所谓的“打架”,而是成为“去吃…”的一个潮州式动词,所以整个词的意思是“去吃潮州菜”。
向一些潮州同学及前辈请教,年轻一代说从未在潮汕地区看过这样招牌的宵夜店,而前辈则说“打冷”从来就有,只是年青人孤陋寡闻。一潮州美食家说,“打冷”是香港式产物,所以在潮汕根本看不到。到底孰是孰非,真的一时难以说清。
美食,不光能满足口腹,还能满足精神上的探索。